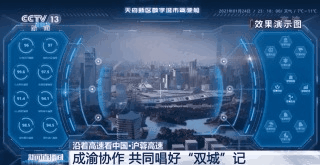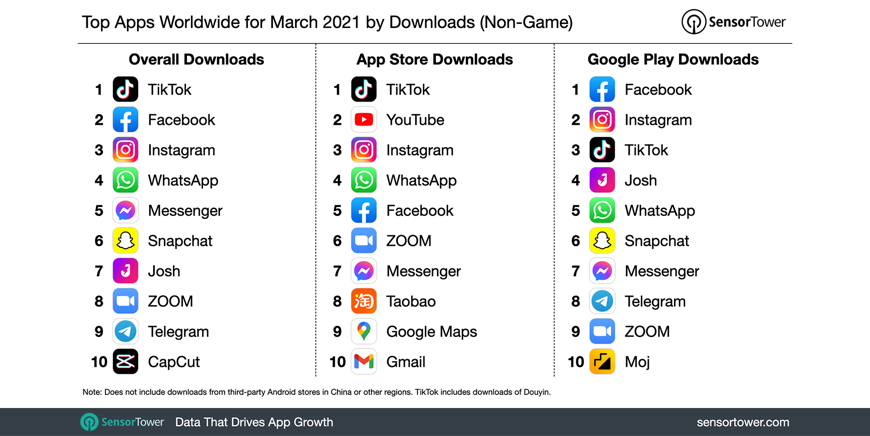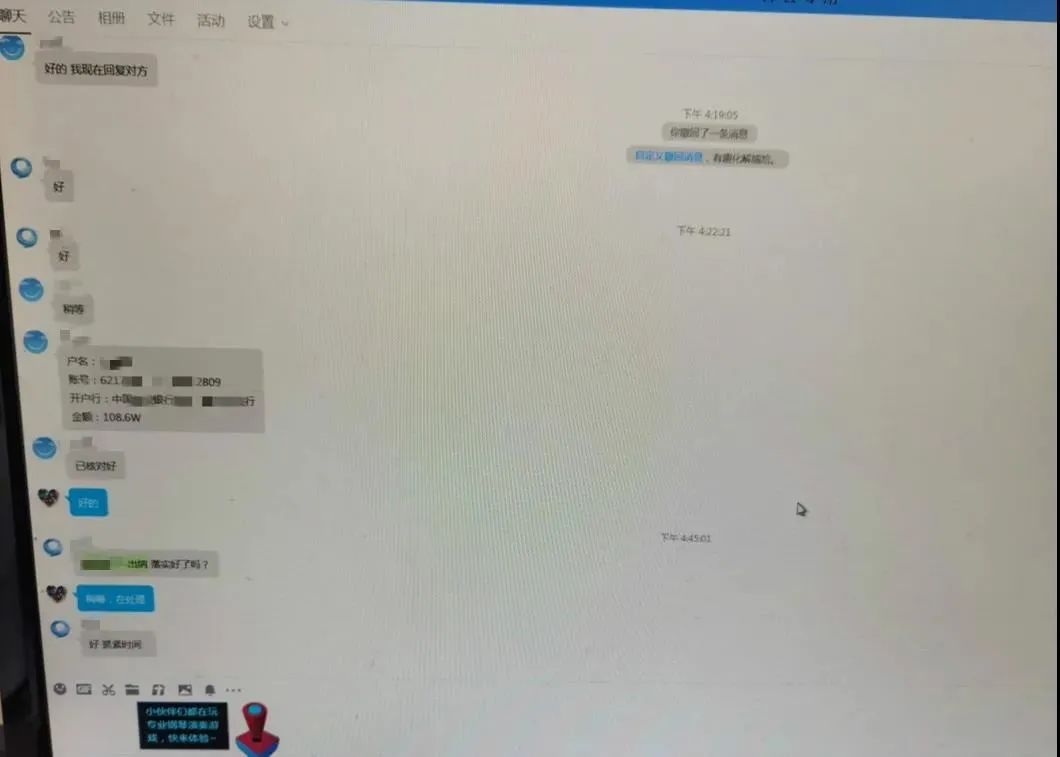原标题:陈建斌保持“追问”

演员陈建斌演绎过多重身份,而导演陈建斌却总是选择成为有些“傻气”的普通人。“傻气”的表象下,他认为不同角色之间真正的共性在于保持“追问”的状态——“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但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需要追问。”
电影是一种记忆装置,创作者不论自觉与否都会将自我的一部分投射到作品之中,我们得以从中窥探他们的不同侧面。在陈建斌看来,角色表现出的勇敢和脆弱同时存在于自己身上,角色也能替他对于困惑发问。
陈建斌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第十一回》,讲述了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事件”被市话剧团改编排演,并与现实生活发生勾连的故事,看似虚假的戏剧世界与现实生活相互交错,相互影响。

角色会塑造人,艺术能够影响现实生活——这是陈建斌的创作观,是他12年的中戏生活、长期的戏剧训练与天然的艺术直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部电影中,话剧演员贾梅怡也被赋予了这种信念,并在追寻角色动机的过程中帮助现实中的人找到了当年的真相。
陈建斌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思考,并选择用幽默而荒诞的故事情节将思考具象化,不过与他钟爱的诗歌一样,故事中依然充满隐喻。在四对情感关系与两场出轨中,各式极具个性的人物纷纷出场,关于家庭关系、永恒的爱情命题,和个人价值的探讨一同发生。
陈建斌认为这部电影很有包容性,“你可以从最简单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那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家庭喜剧,如果愿意也参与到创作之中,故事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01 | 爱情故事
麦子做成面包/葡萄酿成酒
人们若不相爱/就会变成石头
——陈建斌
抛开更复杂的隐喻和线索,《第十一回》中上演了几段不同的情感纠葛,看似都不符合情理,实则是在与观众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在电影中舞台排演与现实生活双线交织。台上是已婚导演出轨懵懂的新人演员,台下是没有地位的凶杀案当事人与家中的悍妇,以及家中未婚先孕的女儿与始终不曾露面的“他”……在陈建斌看来这些或狗血或令人唏嘘的感情经历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故事外壳”,包裹着另一个爱情故事——当年拖拉机下“偷情”而命丧黄泉的男女有何过往。
直到影片结尾,观众会发现那一对从未露面的男女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最重要的人物在这个电影里一秒钟都没有露面”,陈建斌告诉《三声》,这样的结构设计让他“特别着迷”。
多线叙事而又顺畅的故事表达少不了扎实的剧本,这也是“演活一个人物的重要前提”。不同于第一部作品《一个勺子》的个人创作,这次《第十一回》的故事更加复杂,为了讲好一个“雅俗共赏的故事”,陈建斌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五个人,剧本创作长达八个月。饶晓志发微博回忆“在重庆、延庆一遍遍开剧本会打磨剧本的那段日子还历历在目,为了一个片段争论不休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文学小组的成员是陈建斌的“四面镜子”,随着团队不断的碰撞,外在的故事逐渐丰满成型。但最令人着迷的故事线并不是剧本设计之初就明确的,而是创作后期意识到这些故事都围绕着曾经的案件展开,“那条线也就自动地浮现出来”。
这种灵活性在陈建斌的两部作品中有所呼应。《一个勺子》本设计为全员使用地道的西北方言,说重庆话的蒋勤勤并非计划中的人选,友情接演后,剧本就将媳妇“金枝子”修改成同为主角“捡来的”外地人,主角的人设也因此更加统一。在陈建斌看来,有些时候创作中的困难、限制、遇到的障碍,也能帮助自己完善作品。
陈建斌本来计划一人分饰两角,但考虑到操作难度和剧本合理性,便找到了更适合的大鹏来饰演电影中的话剧导演胡昆汀。“我的岁数太大了,如果我演胡昆汀,贾梅怡对应的女演员年龄也得上升,但那样她就不可能是一个第一次排话剧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纯真和勇敢。”
在正式开拍之前,剧团那条线的演员们就已经在话剧团共同排练了两个月,培养了对彼此的默契和信任,陈建斌认为最终他们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得益于那两个月的训练。
在剧本设计里,贾梅怡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怀揣着对艺术的无限憧憬和美好想象,崇拜同样痴迷戏剧的导演。“春夏有一双小鹿一样的眼睛,单纯、清澈,当她凝视你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一样,我觉得贾梅怡也应该有这样一双眼睛,她说契柯夫、莎士比亚那些台词你会相信真的是从她心底涌出来的。”

贾梅怡用那双眼睛仰视着胡昆汀,自然地迷恋上了这位共同探讨艺术、对自己“指导有加”的导演,对他所说的话也都信以为真。休息室里,贾梅怡又一次听导演讲戏,手中把玩的红苹果象征着他们暧昧而危险的爱情正蠢蠢欲动。
02 | 镜子、幕布与屏
树木拥抱树木/一首歌亲吻另一首歌
在铁的道路/有痛苦和欢乐经过
——塞尔努达
红苹果之于禁忌的爱,只是一个“特别浅显的比喻”,但实际上,这部影片中有许多关于戏剧与人生相互折射的隐喻。
贾梅怡、胡昆汀、苟也武这些名字都是导演的有意戏仿,通过调侃剧场里的人名,让他们扮演的角色与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形成对照,“就跟镜子和人生一样,就跟美颜和关掉美颜一样”。但最后戏仿的人却无比真实——贾梅怡的真诚和热爱,驱动她在不断被更改的剧本中一次又一次追寻角色的动机,最终也帮助生活里的人找到了真相。
镜子经常出现在马福礼家中发生对话的餐桌前,也出现在话剧团的休息室中,映射着谎言与事实、假意与真情。那些分别投射出高矮胖瘦马福礼的电视机屏,则只不过是提供了另一种镜像介质下不同的虚实关系。

回归到屏幕外的生活,陈建斌认为“镜子”就是生活里的戏剧。“在生活场景里照镜子,和看电视、电影、戏剧都是一个概念,其实都在看你自己。”听到这番话时我瞥见了他身后的镜子,镜面反射出我的脸,不禁想到我们对电影的解读,甚至对采访内容的理解其实同样是以自己为坐标系度量的。
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总是自我的投射,这一点也体现在电影的角色设计上。他最初之所以也想演胡昆汀,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身上有自己的影子,除了“对戏剧的热爱,以及身上洋溢的不管不顾的劲儿”,陈建斌坦言“他身上的脆弱也是我自己有的,我觉得我并不比他要高明多少,也并不比他坚强多少”。
陈建斌喜欢诗歌,诗和电影都有某种隐喻的属性。在他早期参演的作品《像鸡毛一样飞》中,他曾扮演诗人欧阳云飞,在影片开篇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肖像填满了整个屏幕,冷峻的面庞似审视着所有要消解诗意的观众。
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诗的功能更多是为生活增添美感。家乡的棉花在他眼里,就成为了“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云”。蒋勤勤将要外出参加节目,他就打印出这些年为家人写的诗,集成册,以诗集的形式陪伴在妻子身旁。即使在电影宣发期没有闲暇时间遣词造句,他也要用诗的格式和主要角色来个互动,微博的营销活动也顺势召集影迷以“三行诗”的形式分享观影感受。
“我对文字是很敏感的,很喜欢看那种优美的文字。”陈建斌告诉《三声》,电影名字本来是叫《如是我闻》,但并不是说要拍一个和佛教有关的电影,只是想借用这个词语来表达“我是这样听说的”,“这个故事里讲得都是他们听说的事儿,但这样就特别口语没有美感,古人文字能力真的特别强,‘如是我闻’四个字就概括了”。
如今电影章回体的设置是在后期时才加入的想法,但电影一共就十回,直到正片结束时,“第十一回”的字幕才出现,在陈建斌眼里,这个电影是一个90分钟的预告片,当观众看完电影走进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第十一回。这一设计延续了他对于镜子、幕与屏的理解,“生活和剧场的关系,对应到现实生活场景里就是照镜子和拉开幕布。”
《第十一回》首映当天,陈建斌写了首诗送给观众。他明白艺术作品完成之后,就不再属于创作者而是属于观众了,同时他也非常期待与观众的互动,倾听来自不同视角的声音。在最近一次直播中他说自己密集地看了包括豆瓣、微博等不同平台上的评论,会留心那些精心铺成的细节是否被观众捕捉到。“有时候会得到巨大的满足,如同遇到知音。”
03 | 追寻答案的人
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 / 我解决我的问题
——西川
凶杀案当年以马福礼失手杀死拖拉机下偷情的妻子和情人结案,但由于话剧团的改编影响到了马福礼的家庭与声誉,马福礼便开始四处寻求建议意图夺回尊严。面对不同方向的解决策略他一直重复说“照你说的办”,看似没有自主性,但却一次次获得支持最终也“意外”证明了清白。
在陈建斌眼中,马福礼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缩影。一个作品中的角色是否具有普遍性并不在于他具体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而在于能否以人性的角度对其加以把握。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卖早点的自己就比他聪明,屁哥和白律师其实就跟我们每天在手机里看到的那些鸡汤和新闻是一样的,你不由自主的在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并用各式信息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判断。只是在电影里我用比较具体的方式,展现了资本和知识是怎样改变了他的选择和自我认知。”

当问及“荒诞性”是否贯穿他的创作意识之中时,陈建斌很快就否认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荒诞来形容,可能觉得跟理解的生活(差异太大),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比电影荒诞多了,但是我们司空见惯了,只有当被放大到荧幕中才会意识到怎么这么可笑。你没有带着真正的眼睛去观察,所以你就察觉不到中间的荒诞性。”
荒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客观。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时,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不可思议。在接受了“真实本就荒诞”的语境后,如果观众愿意,甚至可以把电影看成是一部将现实生活元素排列组合的纪录片。
陈建斌认为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每一个个体都是无力而渺小的。作为凶杀案当事人的马福礼,看到的也只是局部的事实,并不了解真相。“他认不清自己看不透生活,难道我们就可以吗?”这无关贫穷与富有,而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无法认清全貌,但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上的不足,才会对于生活和自我有疑问。陈建斌作为创作者将自己的疑问投射到角色身上,让角色代替自己追寻答案。所以从第一部导演作品《一个勺子》到如今的《第十一回》,“拉条子”与马福礼虽都看似痴傻,但同时非常善良,并且一直保持着“追问”的状态。
这种追问本身也蕴含着诗性瞬间。波德莱尔曾经说,“只要人们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中去,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他们就会知道,诗歌除了自身外并无其他目的。”
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十几岁的陈建斌在看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时也无法理解其中深意,但是电影艺术带来的巨大震撼勾起了他日后对于电影的兴趣。他形容自己是“职业影迷”,在漫长的追寻艺术的过程中,被无数经典不断滋养,潜移默化的积累下,他成为演员,成为编剧,成为导演。
“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但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需要追问。”在陈建斌看来,对于一些人而言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答案”就并不重要,但可能对于少数人而言,即使找不到“答案”,寻找的过程也很重要。即使彼此对问题看法不一致,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回答所带出来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
那些在“追寻答案”的人是陈建斌一直以来想记录描写的对象,只要被打动,他就会为这些人和事“作诗”,以文字,以影象。而创作的过程包裹着思考与追问,留下了他个人生命的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