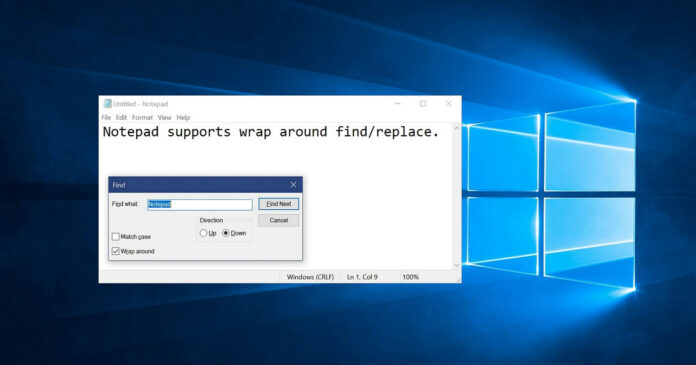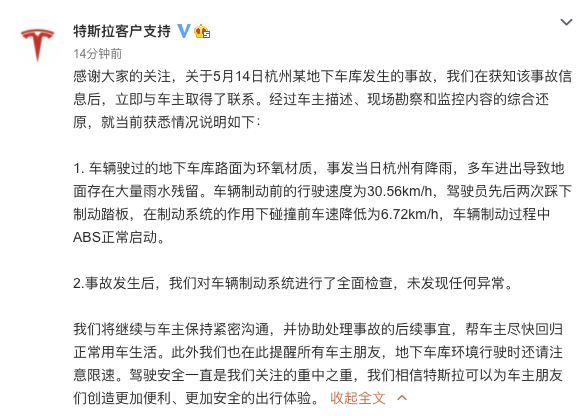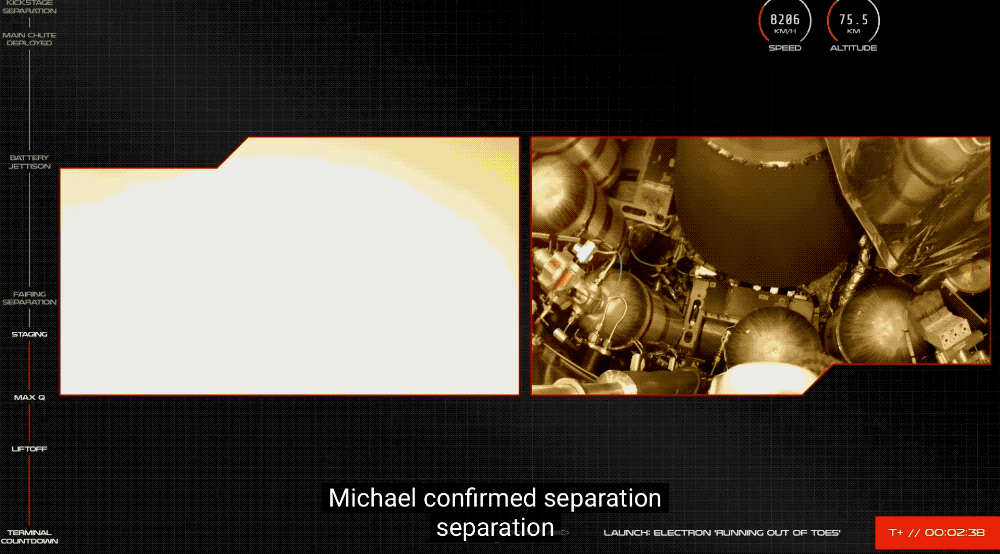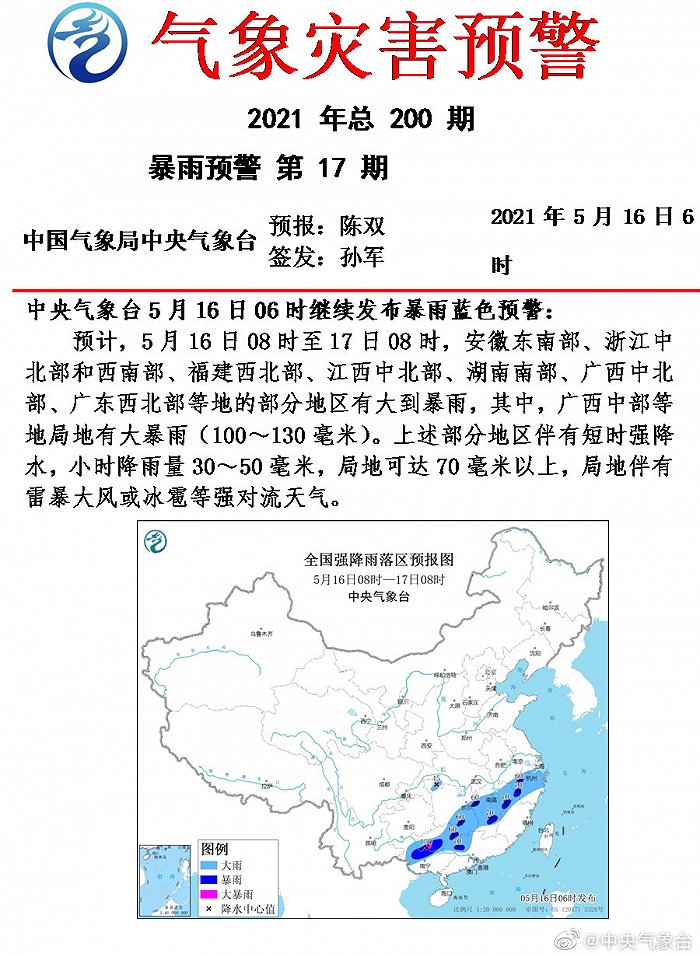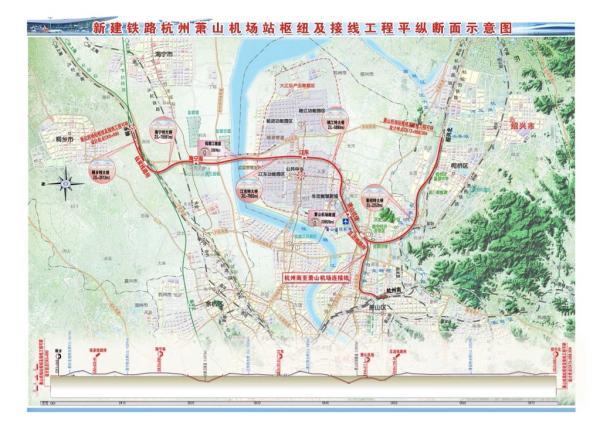原标题:从祖先到婴孩,从宗教到科学:为什么想象力是人类最宝贵的生存工具?
 图片来源:kuruneko / Shutterstock
图片来源:kuruneko / Shutterstock柏拉图在其《泰阿泰德》中对苏格拉底说,“这种感染力是哲学家所特有的:它就是惊叹与好奇(thaumazein)。而哲学的出发点莫过于此。”这个词包含词根thauma(意为“奇迹”),thaumaturgy(意为“魔术”)亦包含此词根。thaumazein经常被翻译为“惊奇”。哲学诞生于惊奇,混合着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来自于我们面对令我们着迷、超越了我们且令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的时刻。亚里士多德明确写道,人类从提出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越发对复杂的事物感到惊奇,最后通过研究月亮、太阳和星星,以及探寻宇宙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来感受惊奇。
当我们看着满天星斗时,我们得到的惊奇感是一种强大的感觉,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强烈的、甚至会触动情感的体验。这种感觉将我们与之前的几千代人共有的那种古老的、惊奇的回响联系起来。但也许这种感觉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种根深蒂固的、紧迫的、原始的、几乎与生俱来的寻求重大问题答案的需求的起源。
当代哲学家埃马努埃莱·塞维里诺(Emanuele Severino)再次提出了这个主题,他坚持强调将thauma翻译为“混合着痛苦的奇迹”。这样,我们就恢复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而知识将作为“一种解毒剂,消除突然出现的毁灭性事件所引发的恐怖”。
 神奇到令人恐惧:宇宙惊人的大小和范围激发了一种痛苦的惊奇感,这种感觉和独眼巨人给你带来的感觉一样。图片来源:DomCritelli / Shutterstock
神奇到令人恐惧:宇宙惊人的大小和范围激发了一种痛苦的惊奇感,这种感觉和独眼巨人给你带来的感觉一样。图片来源:DomCritelli / Shutterstock事实上,荷马也是这样使用这个词的,他在描述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时提到了thauma——这个独眼巨人肢解并吞噬了尤利西斯不幸的同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所隐含的与痛苦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看到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个巨大的生物,就会引起人的惊奇和恐惧。这个巨人,象征着自然界桀骜不驯的力量,他让人对他不可思议的力量感到惊奇,同时也让我们因自己的脆弱和无意义感而感到深深的苦恼。自然界释放的力量,如火山的爆发或可怕的飓风,同时让人着迷和恐惧,因为它们把我们的世界打得粉碎,或在瞬间吞噬我们。在这个更大的画面中,像我们这样渺小、脆弱的生命所扮演的角色,不断地暴露在痛苦和死亡中,我们是完全微不足道的。
就是在这种时刻,神话、宗教、哲学或科学的叙事、解释可以安慰和安抚我们,给不可控制的系列事件以秩序,并以这种方式保护我们免于感到痛苦和恐惧。在这种叙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它赋予存在的大循环以意义。我们得到了安慰,因为我们感到受到了保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随之消失。我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会结束,而且,与我们周围的物质结构的漫长的进化周期相比,我们会很快结束。但是,当了解到这个整体服从于我们的叙述中所描述的秩序时,我们就会感到安心。
几百万年来,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生活的严酷性。仅仅从几十年前起,且仅对世界上的部分人口而言,这种极端脆弱和完全不稳定的体验才渐渐消退。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仍然感受到那种祖传的痛苦。我们都像《惊悚末日》中的小主人公利奥一样,在面对即将降临地球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时,寻求保护和慰藉。他需要有人告诉他:不要害怕,你不会有事的。他在姨妈贾斯汀身上找到了这种慰藉。贾斯汀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当所有理智和正常的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她表现得最清醒,并拿出了足够的韧性来保持她的人性。她和孩子用于寻求庇护的小帐篷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即将到来的灾难,但直到碰撞前的最后一刻,在姑姑温暖的怀抱中,听着姑姑平静的讲述,利奥感到很安全。
 我们都像《惊悚末日》中的小主人公利奥一样,在面对即将降临地球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时,寻求保护和慰藉。图为《2012》剧照。图片来源:Columbia Pictures
我们都像《惊悚末日》中的小主人公利奥一样,在面对即将降临地球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时,寻求保护和慰藉。图为《2012》剧照。图片来源:Columbia Pictures艺术、美、哲学、宗教、科学,总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魔法帐篷,我们自古以来就迫切需要它。它们很可能同时诞生,是象征性思维的不同表达方式。不难想象,文字的节奏和音韵会促进起源故事的传播,歌曲和诗歌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类似的事情可能也发生在了洞穴墙壁上描绘的标志和符号上,它们在形式上越来越复杂、完美;在伴随着哀悼的仪式和典礼中,有规律的声音往往伴随着身体的律动或智者、萨满的歌声。科学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episteme(意为“知识”)和techne(意为“技艺”)相伴相生并不是偶然的,知识与生产器具、工艺品、机器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对希腊人来说,techne,英语中“技术”一词(technique)的根源,也表明了工匠和艺术之间的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在生产燧石刀的时候,技术上的要求——即打造一件锋利的、易于操作的切割工具,与美学上的要求——即生产出对称的、精细的、完美平衡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总之,它应当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
这些迫切的需要似乎已经构成了几千年来在地球上行走的所有人类群体不可抗拒的东西。即使是在婆罗洲或亚马逊一些森林中的最孤立的偏远部落,也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仪式、特定的艺术表达形式和他们自己的象征宇宙,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关于他们起源的总体故事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这样的叙事,不仅不可能建立伟大的文明,而且即使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也无法生存。这就是我们星球上的所有人类群体都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的原因。
 仪式、特定的艺术表达形式和他们自己的象征宇宙,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关于他们起源的总体故事作为支撑。图为埃及墓中壁画。图片来源:British Library
仪式、特定的艺术表达形式和他们自己的象征宇宙,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关于他们起源的总体故事作为支撑。图为埃及墓中壁画。图片来源:British Library文化,是对自身最深层根源的认识,是一种超级力量,让我们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也能生存。想象一下,两个原始的社会群体,两个尼安德特人的小部族,在那个时代的冰天雪地的欧洲相互隔绝地生活。现在,假设这两个群体中的一个偶然发展出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通过仪式和典礼将它们世代营造和延续,并将它们在洞穴壁画中直观体现,而另一个群体没有这样做,即没有发展出任何复杂的文化形式。现在,让我们假设两个群体都遭遇了灾难:一场洪水或一段比往常更极端的寒冷时期,或一次凶猛的野兽袭击,只留下一个孤独的幸存者。在这两个群体中,这个最后幸存的人将不得不克服无数的危险,面对各种困难,也许会迁徙到其他地区,甚至需要躲避人类的敌意。两者中哪一个会表现出最强的复原力?谁会有更多的生存可能?
一个创造的故事,一段关于起源的叙述,能给你在被击倒时重新站起来的力量,给你在最绝望的情况下继续忍受的动力。我们紧紧抓住给予我们保护和身份的稻草,我们找到了抵抗和继续的力量。我们将自己和家族中的其他人置于始于属于遥远过去的一长串事件中,这使我们得以想象未来。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可以把当下可怕的变幻无常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使痛苦有意义,帮助我们克服最可怕的悲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几千代之后仍然在为艺术、哲学、科学赋予价值。因为我们就是这种自然选择的继承者。那些最有条件发展象征宇宙的个人和群体,享有显著的进化优势,我们正是他们的后代。

把当下可怕的变幻无常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使痛苦有意义,帮助我们克服最可怕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几千代之后仍然在为艺术、哲学、科学赋予价值。图为《一道惊雷》。图片来源:Birmingham Museums Trust
我们不该惊讶于象征性和想象力的力量。成为社会动物的条件,是比我们生活在有组织的个人群体中这一简单事实更深刻和内在的东西。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在世界各地启动了非常雄心勃勃的项目来研究人类大脑的功能。这些项目都是资金和资源充足的多学科项目,它们调用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详细了解大脑的一些基本机制,科学家使用电子技术模拟神经元网络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努力对于理解大脑运作的某些动态非常有用。那么,为什么那些欢迎技术发展的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为了创造一个人工大脑而扩大这些基本结构是没有意义的呢?
这不仅仅是克服重大技术困难的问题。我们的头盖骨承载着近9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能与相邻的神经元建立多达10000个突触。这个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够建造一个如此复杂的电子设备、能够在技术上再现我们的大脑结构,它仍然不能成为一个人类。这份忠实的拷贝中缺少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电子形式复制它的难度是无法估量的。这份拷贝中缺少的,是与其他人类大脑的互动,即通过语言、身体和情感关系进行的斡旋。换句话说,一个人通过他人对其的感知,在他人的眼中和与他们的情感交流中,通过与社会群体中与我们有关系的其他人类互动,才成为人类。
新生婴儿柔韧的大脑是在与照顾她的成年人所调和的世界发生的关系中形成的,一切始于母亲的目光。一个婴儿看着喂他的人的眼睛,他们的关系发生反应,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他的突触。我们称为人脑的东西,是从这样的可塑性系统之间的互动中诞生的,这个系统能够适应并被来自外部的刺激所塑造,并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建立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由希望和欲望滋养,它们甚至在胚胎母体里成型之前就开始了。新生命在出生前就与父母的愿望对话,并与过去和来到它面前的人类接触。她通过幻觉被投射到未来,这种幻觉建立了围绕新生命的小社会群体:祖父母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发现了与祖先故事有关的相似之处,旧的恐惧和新的期望由此产生。任何电子设备都不可能重现这一切。
为了证实我们试图描述的东西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想想那些在野外迷路或被遗弃,在动物的陪伴下长大的幼童的例子。他们的大脑在结构上与同时代的孩子完全相同,但由于缺乏与人类的接触,他们未能成为完全的人。无论后来有多少接触和对于康复的尝试,都无法填补早期互动缺失造成的空白。
 新生婴儿柔韧的大脑是在与照顾她的成年人所调和的世界发生的关系中形成的,一切始于母亲的目光。图片来源:Minnie Zhou/Unsplash
新生婴儿柔韧的大脑是在与照顾她的成年人所调和的世界发生的关系中形成的,一切始于母亲的目光。图片来源:Minnie Zhou/Unsplash当想象力和叙述在一个群体中得到培养时,它们就会成为强有力的生存工具。谁能倾听和想象他人的经验,谁就能以这种方式获得真正的知识。叙事浓缩了前几代人长期积累的经验,使我们能够体验和理解——它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千百种不同的人生。想象力让我们体验到情感和恐惧,悲伤和危险,群体的价值观;有助于维护想象力的规则,维护和管理想象力发展的规则,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被重申和记忆。
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先进的群体中被发展和鼓励的想象力,是我们有史以来发展出的最有效的武器。科学也起源于想象力:由于选择将自己的叙述建立在实验验证的基础上,它得出了更多创造性的技术和更大胆的设想。为了探索物质和宇宙中更隐蔽的角落,科学不得不克服各种限制,并将起源的故事变成一场非凡的旅程。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经常需要改变人类对事物的思考方式的模式。在整个历史上,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古希腊哲学家)到海森堡(Heisenberg,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和爱因斯坦,它已经多次这样做了,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科学不断进步,它改变了我们看待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都会改变。不仅仅是因为由此产生的新仪器和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改变范式,就会让我们所有的关系发生改变。当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会随着我们的艺术和哲学而改变。理解和预测这些变化,即是拥有了建立更好的人类社会的工具。
由于这个原因,艺术、科学和哲学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学科,它们使我们作为人类具有连续性。这种源于我们最遥远的过去的统一的世界观,仍然是应对未来挑战的最合适的工具。
本文作者Guido Tonelli是比萨大学的普通物理学教授,也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访问科学家。新作《创世纪:万物起源的故事》(Genesis: The Story of How Everything Began)由Erica Segre和Simon Carnell翻译。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