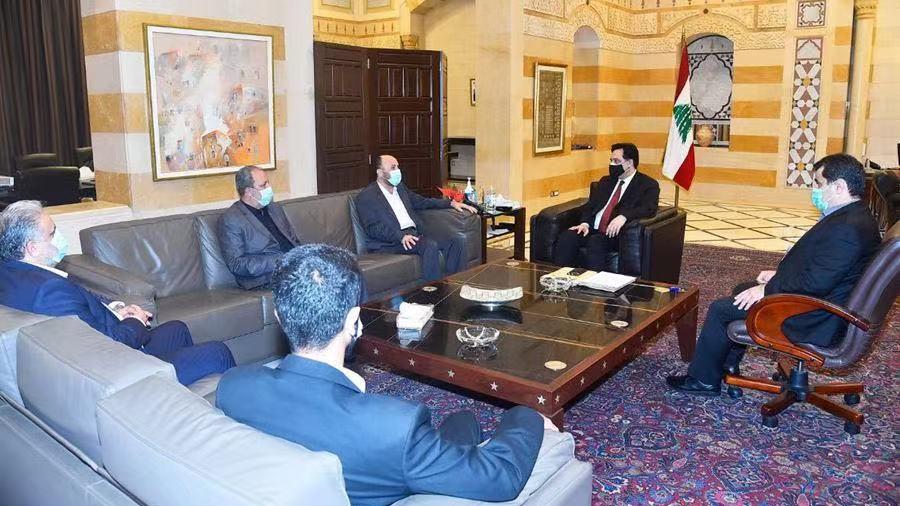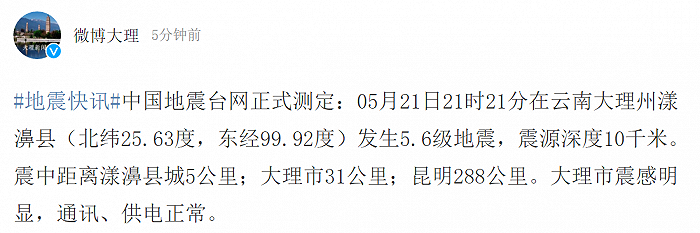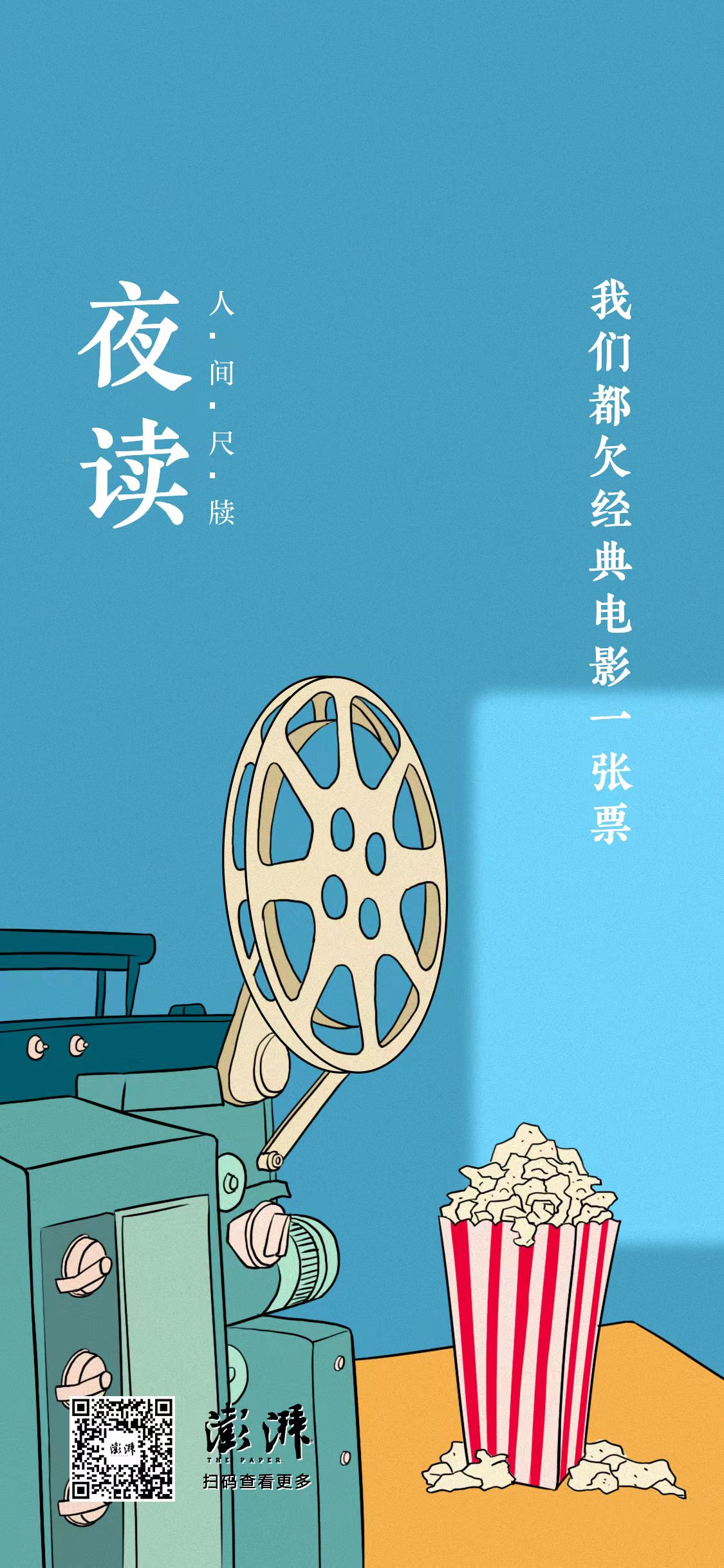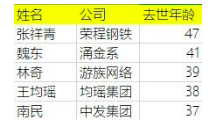原标题:邯郸路220号点滴
原创 fanggong 晏秋秋 收录于话题#晏秋秋:魔都私家地理61个
文/晏秋秋
邯郸路的门牌号码,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
隐约记得,邯郸路220号出来,下一个号码就是400号。出门向左,是五角场。出门向右,是大柏树。
 最近3年,“魔都私家地理”的笔触,就在邯郸路上滑来滑去,五角场写过了,大柏树写过了,却从来不敢写复旦大学。复旦大学这个题目太大了,盛大到了缥缈。虽然我从来都是以复旦为荣,虽然我很乐于用文字表达自己,但说实话,冲动却怂。
最近3年,“魔都私家地理”的笔触,就在邯郸路上滑来滑去,五角场写过了,大柏树写过了,却从来不敢写复旦大学。复旦大学这个题目太大了,盛大到了缥缈。虽然我从来都是以复旦为荣,虽然我很乐于用文字表达自己,但说实话,冲动却怂。 有一年采访全国“两会”遇到复旦“一哥”,他很客气地说,希望我为母校多写点东西。我一听之下,顿时有点手足无措,我能写什么呢?只能低下头去,“嗯”上几句。那句客气话距今已经十几年了,我一篇也写不出来。
有一年采访全国“两会”遇到复旦“一哥”,他很客气地说,希望我为母校多写点东西。我一听之下,顿时有点手足无措,我能写什么呢?只能低下头去,“嗯”上几句。那句客气话距今已经十几年了,我一篇也写不出来。 昨天晚上,有粉丝说,我在邯郸路220号读了4年本科,工作后还读了3年在职的硕士,总有东西可写吧。至少,总有一些个人的记忆点滴。哪怕这些点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多少还有些趣味,能够让人们知道,25年前的复旦大学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有点心动。也就有了这篇邯郸路220号的个人记忆。这是一篇勉强的“魔都私家地理”,对我个人来说,像还债。
昨天晚上,有粉丝说,我在邯郸路220号读了4年本科,工作后还读了3年在职的硕士,总有东西可写吧。至少,总有一些个人的记忆点滴。哪怕这些点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多少还有些趣味,能够让人们知道,25年前的复旦大学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有点心动。也就有了这篇邯郸路220号的个人记忆。这是一篇勉强的“魔都私家地理”,对我个人来说,像还债。 上面说了,我在复旦读了7年书。不过,我呆在邯郸路220号的时间,可远没那么长。
上面说了,我在复旦读了7年书。不过,我呆在邯郸路220号的时间,可远没那么长。我算个蛮有名的“逃课大王”吧。大四开始,我长时间在新民晚报体育部实习。我的宿舍床位,也慷慨地向其他同学、或者同学的同学开放。有一天,我接到某老师的电话,问是不是好久没去学校了。我嗫嚅地说:大概一个月吧。某老师对我提出了严厉的要求:每个月必须来一次学校。
新闻系的老师多好啊。 读硕士时,有一门课,我因为一直出差,从头到尾就没有参加过。考试前最后一堂课,我凭记忆提前30分钟赶到课堂,却空无一人。原来课堂早就换了。
读硕士时,有一门课,我因为一直出差,从头到尾就没有参加过。考试前最后一堂课,我凭记忆提前30分钟赶到课堂,却空无一人。原来课堂早就换了。 我打听清楚,又跑到新课堂,见教室里已有一人坐下,于是询问:同学,这里是上XX课的地方吗?只见对方缓缓抬起头来:“同学,你是上XX课的吗?”我说是。然后对方说:“你上XX课,不认识老师吗?”现在年轻人说的“社死现场”,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但是,这门课我还是拿了B+。
我打听清楚,又跑到新课堂,见教室里已有一人坐下,于是询问:同学,这里是上XX课的地方吗?只见对方缓缓抬起头来:“同学,你是上XX课的吗?”我说是。然后对方说:“你上XX课,不认识老师吗?”现在年轻人说的“社死现场”,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但是,这门课我还是拿了B+。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记得有一门公共课程,我有通不过的危险。当晚,在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就摸到教授家中,和他大聊足球,还委婉解释自己缺课较多,主要是实习较多出差。教授笑眯眯地听着,那笑容很慈祥。我从来没把这作为一篇文章来写,所以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太“自由”了。在这里强调一下,我的记忆可能偏差,我的文笔有点夸张,我的举例可能不是事实,我的表态不太恰当——为了避免麻烦,我不会具体写到人名,但我要表达我的感觉。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记得有一门公共课程,我有通不过的危险。当晚,在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就摸到教授家中,和他大聊足球,还委婉解释自己缺课较多,主要是实习较多出差。教授笑眯眯地听着,那笑容很慈祥。我从来没把这作为一篇文章来写,所以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太“自由”了。在这里强调一下,我的记忆可能偏差,我的文笔有点夸张,我的举例可能不是事实,我的表态不太恰当——为了避免麻烦,我不会具体写到人名,但我要表达我的感觉。 复旦新闻系的老师们,是很好很好的。
复旦新闻系的老师们,是很好很好的。离开邯郸路220号,我一头扎入社会,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的老师。
初到邯郸路220号,一个宿舍6人,我们是一群充满好奇的小伙子。
报到后第二天,我们跑到隔壁寝室,向95级的师哥请教。门没关,只见一人慢慢从床上爬起,顶着睡乱的蓬松头发,耐心回答我们关于新闻系的问题。
师哥很逗,第一句回答是:新闻系的生活,就是无所事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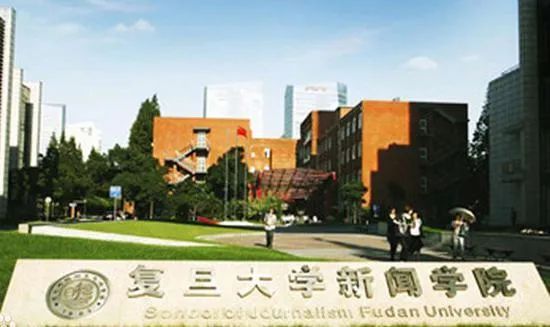 至此知道,这个系的学生,自我表达的意识都很强。师哥一直保持着个性,工作后也是这么的逗,总是让我有一种不合时宜的亲切感。
至此知道,这个系的学生,自我表达的意识都很强。师哥一直保持着个性,工作后也是这么的逗,总是让我有一种不合时宜的亲切感。哦,对了,还有很个性的师弟,总是在熄灯以后,一个人抱着吉他,在走廊里唱歌。每当这个时候,想睡的人就嫌吵,大家会展开骂战,师弟从来不怂,却好像一次也没打起来。
 对了,有一个师妹,是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她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拉着她下棋,不和棋不能走。所以我现在虽然连国际象棋规则都忘得差不多了,却总是能说一句:我和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下了平手!
对了,有一个师妹,是国际象棋的特级大师。她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拉着她下棋,不和棋不能走。所以我现在虽然连国际象棋规则都忘得差不多了,却总是能说一句:我和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下了平手! 大一时,我们寝室迎来了唯一一次和外校的“联谊”。对方是上海外国语大学6个女孩子。寒暄过后,我们腼腆得像沉默的二哈,对方女生忍不住说了一句:“复旦新闻系的男生,就这么沉默吗?”我们面面相觑,于是下一个节目,就是盛邀女生们玩当时很火的“扫雷”游戏。总算,气氛热闹了一点!
大一时,我们寝室迎来了唯一一次和外校的“联谊”。对方是上海外国语大学6个女孩子。寒暄过后,我们腼腆得像沉默的二哈,对方女生忍不住说了一句:“复旦新闻系的男生,就这么沉默吗?”我们面面相觑,于是下一个节目,就是盛邀女生们玩当时很火的“扫雷”游戏。总算,气氛热闹了一点! 那个时候,寝室每天晚上是要熄灯的。大学生的精力旺盛,熄灯之后,却仍有很多事可做。
那个时候,寝室每天晚上是要熄灯的。大学生的精力旺盛,熄灯之后,却仍有很多事可做。 有个同学,喜欢熄灯之后,到东区外的小吃摊上,去买上一盆炒面。黑暗之中,听人吸面条,香味入鼻,那滋味不好受。有好几次,我也去买上一盒,特别响地吸着面条,仿佛获得了双倍的快乐。那个时候我很幼稚。同学从老家带来了花生肉酱,好意与我分享。没想到我竟越吃越爱吃,差一点把肉酱全部吃完。
有个同学,喜欢熄灯之后,到东区外的小吃摊上,去买上一盆炒面。黑暗之中,听人吸面条,香味入鼻,那滋味不好受。有好几次,我也去买上一盒,特别响地吸着面条,仿佛获得了双倍的快乐。那个时候我很幼稚。同学从老家带来了花生肉酱,好意与我分享。没想到我竟越吃越爱吃,差一点把肉酱全部吃完。 我们都是淘气的小伙子。有几次借着放假的契机,跑到女生宿舍去,和女同学坐在一起闲话。有人点上蜡烛,有人背着白话诗,那真是一个纯粹的年代。
我们都是淘气的小伙子。有几次借着放假的契机,跑到女生宿舍去,和女同学坐在一起闲话。有人点上蜡烛,有人背着白话诗,那真是一个纯粹的年代。忘了说一句,女生寝室看门的老大娘凶啊。我进入社会工作后,每次见到手握一点点权力就趾高气昂的人,脑海里总是出现老大娘的身影。
对不起,我知道,老大娘是为了我们好! 邯郸路220号的生活,真的是太好玩了。
邯郸路220号的生活,真的是太好玩了。有一位师哥接到了家长的来信,信中说:“我知道,你们复旦大学距离上海申花的江湾基地不远,我希望你能好好读书,不要去追星,追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但足球还是我们最热衷的项目。院系的七人制足球赛,踢得不亦乐乎。我在大一时还能混混,大二时隔壁系有的同学奇迹般地第二次发育,那我就踢不过了。
 有一段时间,要求学生早起跑步。跑到相辉堂附近,再跑回宿舍,敲一个章。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我是真的觉得这有利于身体,积极响应。但从第四天开始,我还是觉得,与其跑步,不如去苏州或杭州玩,比较理想。
有一段时间,要求学生早起跑步。跑到相辉堂附近,再跑回宿舍,敲一个章。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我是真的觉得这有利于身体,积极响应。但从第四天开始,我还是觉得,与其跑步,不如去苏州或杭州玩,比较理想。 但有一件事,我是坚持做了一个学期的,那就是大冬天洗冷水澡。那是受了毛泽东“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每天熄灯之后,带着脸盆拖鞋,到一楼的澡堂冲冷水澡。看门大爷急急地说:“你们不要命了!”自己却只是淡淡一笑,感觉很有毅力。
但有一件事,我是坚持做了一个学期的,那就是大冬天洗冷水澡。那是受了毛泽东“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每天熄灯之后,带着脸盆拖鞋,到一楼的澡堂冲冷水澡。看门大爷急急地说:“你们不要命了!”自己却只是淡淡一笑,感觉很有毅力。 每次洗完澡,摸索着回到寝室,躺到床上。少倾,一股暖流在周身流动,浑身舒坦,并能很快进入梦乡。可惜的是,我的个人感受,越是洗冷水澡,越是容易睡懒觉。所以身心的健康,有时候很难两全其美。
每次洗完澡,摸索着回到寝室,躺到床上。少倾,一股暖流在周身流动,浑身舒坦,并能很快进入梦乡。可惜的是,我的个人感受,越是洗冷水澡,越是容易睡懒觉。所以身心的健康,有时候很难两全其美。 去食堂吃饭,也是一门学问。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记不起一份经典的大排青菜要多少钱了。反正去舀免费的蛋花汤,那是有口诀的——溜边沉底,轻捞慢起。有一个外系的哥们,家里穷,每天买5个馒头,对付三餐。据他后来说,完全是靠着食堂里这一碗又一碗免费的汤,混的“水饱”。
去食堂吃饭,也是一门学问。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记不起一份经典的大排青菜要多少钱了。反正去舀免费的蛋花汤,那是有口诀的——溜边沉底,轻捞慢起。有一个外系的哥们,家里穷,每天买5个馒头,对付三餐。据他后来说,完全是靠着食堂里这一碗又一碗免费的汤,混的“水饱”。 复旦东区边上,有一条铁路。铁路边有几个小饭馆,一度卖过碗装的啤酒。我和几个哥们去喝酒,一个哥们早走。我们出来后,却发现他抱着一棵小树苗,站着睡着了。走近一看,这家伙对着小树方便,系上皮带,却将小树苗圈在了里面,于是走也走不了,就此睡着了。
复旦东区边上,有一条铁路。铁路边有几个小饭馆,一度卖过碗装的啤酒。我和几个哥们去喝酒,一个哥们早走。我们出来后,却发现他抱着一棵小树苗,站着睡着了。走近一看,这家伙对着小树方便,系上皮带,却将小树苗圈在了里面,于是走也走不了,就此睡着了。生活多么精彩啊,真像戏剧里的情节。
也是在这样的小饭馆,我看到一名复旦的老师叫了一份菜汤面,特地强调“三个荷包蛋”,这要多少钱啊,哈哈,年轻的心灵第一次有了金钱的烙印。 在邯郸路220号的一天,我看到了老校长谢希德在校园里走着,阳光从树荫洒下来,透照在地下,斑斑点点。这是一个很亲切,很善良的老太太。小卖部的员工和她打招呼,她笑盈盈地挥手回答。
在邯郸路220号的一天,我看到了老校长谢希德在校园里走着,阳光从树荫洒下来,透照在地下,斑斑点点。这是一个很亲切,很善良的老太太。小卖部的员工和她打招呼,她笑盈盈地挥手回答。我离开邯郸路220号已有十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