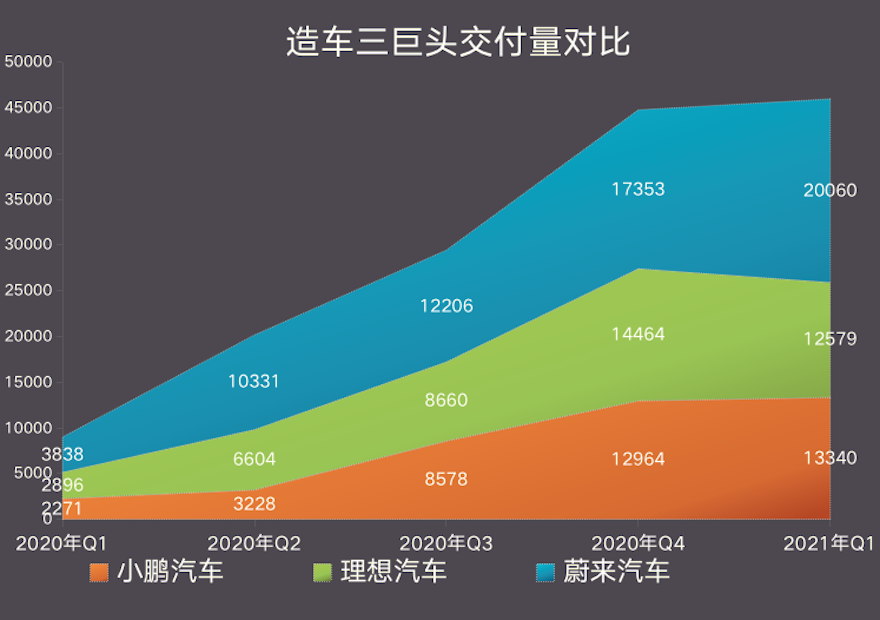原标题:两任妻子捐出珍藏,我们才看到他的传奇一生
2021年5月,
抽象艺术的开山鼻祖——
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
的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登陆上海,
这也是这位20世纪大师在整个亚洲
最具规模的一次亮相。

康定斯基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富二代出身,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30岁裸辞,转行投身艺术,
42岁才开办首场个展;
拥有将视觉连通音乐的“联觉”能力;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四处流亡,
晚年却爱上了中国古代青铜器……
他的恋爱场场精彩,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分别将他生前的作品慷慨捐献,
才让这个时代的观众得以一睹原作。

这次回顾展,
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特展,
以5个篇章,
按时间顺序呈现康定斯基丰富的一生,
近百件珍贵原作和手稿,
1:1复刻的门厅壁画,
还有全球首次展出的康定斯基私人收藏:
与中国相关的艺术品、出版物将分别呈现。
跟随一条,走进康定斯基的艺术世界。
撰文 陈沁 责编 陈子文


15幅一组的谷垛,在四季与晨昏流转间,光影、色彩不断变迁。他忽然意识到,绚丽的色彩竟可以从物体中被解放出来。对他而言,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
一场莫奈的展览,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不久后,康定斯基决定放弃前途无量的法学教授教职,去慕尼黑追逐艺术之梦。半路出家的他野心勃勃,但为人矜持、严肃,没有同时代的毕加索身上的盛气凌人。
青年时期的康定斯基身形瘦削,常年一袭西装。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玻璃眼镜,眼神清亮坚毅。

这位抽象艺术大师,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遇到了两段爱情,一段“禁忌之恋(师生恋)”,一段“老少恋”。
据说康定斯基一恋爱,就会将抽象艺术抛诸脑后,为恋人画出一幅幅具象作品。这两个女人手里,珍藏着贯穿康定斯基一生的画作。
一战期间,51岁的康定斯基,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27岁的俄国女人妮娜(Nina Andreevskaya),迅速与之闪婚,并与妮娜共度了27年的婚姻生活。康定斯基逝世后,妮娜没有再婚,她向蓬皮杜中心捐赠了康定斯基一战后的大部分作品。
这场将在上海持续4个月的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盛宴,便得益于妮娜的慷慨捐赠和遗赠。 他的父亲是西伯利亚的茶叶经销商,母亲是蒙古贵族后代,从小家境优渥,没体验过烦恼的滋味,是个“被宠坏”的小孩。家庭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自幼被送去学钢琴、大提琴。在莫斯科大学,他拿下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一切顺风顺水。
他的父亲是西伯利亚的茶叶经销商,母亲是蒙古贵族后代,从小家境优渥,没体验过烦恼的滋味,是个“被宠坏”的小孩。家庭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自幼被送去学钢琴、大提琴。在莫斯科大学,他拿下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一切顺风顺水。
如果不是被莫奈的画所“误”,康定斯基的名字可能会被写进法学史。而他的艺术之路,也并不平坦。30岁前往德国慕尼黑学绘画,他从学生做起,花了3年,才正式考进慕尼黑美术学院。
19世纪末的慕尼黑,虽不像巴黎一般大师云集、风云际会——印象派、后印象派,象征主义、野兽派,各种艺术思潮空前活跃——但革新的浪潮已在酝酿。
 作为莫奈的铁杆粉丝,康定斯基积极参与当时的新艺术运动。像印象派画家一样,他看重对现实物体的感知,以调色刀在画布上涂抹色块来作画,还尝试了蛋彩画、油画写生、木刻版画等艺术形式。
作为莫奈的铁杆粉丝,康定斯基积极参与当时的新艺术运动。像印象派画家一样,他看重对现实物体的感知,以调色刀在画布上涂抹色块来作画,还尝试了蛋彩画、油画写生、木刻版画等艺术形式。 在这个山水环绕的巴伐利亚小镇,康定斯基和当时的恋人蒙特(Gabriele Münter)度过了整个夏天。这对恋人每日形影不离,一道外出散步、写生,蒙特甚至还在小镇买下了一栋房子。
在这个山水环绕的巴伐利亚小镇,康定斯基和当时的恋人蒙特(Gabriele Münter)度过了整个夏天。这对恋人每日形影不离,一道外出散步、写生,蒙特甚至还在小镇买下了一栋房子。 康定斯基凝望着大自然丰富的色彩,沉浸在群山淡蓝色的光影里,开始逐渐脱离具象元素,转而使用简单的形状,形成自己的抽象风格。
康定斯基凝望着大自然丰富的色彩,沉浸在群山淡蓝色的光影里,开始逐渐脱离具象元素,转而使用简单的形状,形成自己的抽象风格。
高饱和度的色彩,可以明显看到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野兽派的影响,画布成为形状和颜色之间多重对立的舞台。
这一时期,他还和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等艺术家一起成立了“蓝骑士”艺术家团体,轰动一时。 《即兴III》中,拉长的笔触,随意的色彩,火红的天空,显现出一名骑士骑着绿色的马,正踏上一座桥。
《即兴III》中,拉长的笔触,随意的色彩,火红的天空,显现出一名骑士骑着绿色的马,正踏上一座桥。 《有红迹的画》作于1914年,在一个完整的正方形中,色彩的透明度和扩散效果令人眼前一亮,反差强烈的色块在旋转的空间中逐渐散开。画面已抽象得完全看不出对应的现实物了。
《有红迹的画》作于1914年,在一个完整的正方形中,色彩的透明度和扩散效果令人眼前一亮,反差强烈的色块在旋转的空间中逐渐散开。画面已抽象得完全看不出对应的现实物了。
关于康定斯基的抽象探索,还有一则“著名轶事”。
一个平淡的午后,康定斯基正在工作室里创作,无意中,他瞥见一幅从没见过的画,凝视了许久后,他才反应过来,原来那是自己的作品,只是被挂反了。
这一偶然的凝视,意义非凡。倒置的画使得画中的“主体”无从辨认,但他忽然意识到,颜色和形状本身有其“难以形容的美丽”。于是,他决定打破经典的图形代表系统,将形式和色彩独立出来。 1910年前后,是西方现代艺术革命的时代,法国“立体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意大利“未来主义”正风起云涌。康定斯基保持着一贯的专注与冷静,闭起门来,写作他最著名的艺术著作《论艺术的精神》。
1910年前后,是西方现代艺术革命的时代,法国“立体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意大利“未来主义”正风起云涌。康定斯基保持着一贯的专注与冷静,闭起门来,写作他最著名的艺术著作《论艺术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他独创了“联觉(知觉混合)”理论,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诠释他的抽象艺术。
“联觉”有点儿像康定斯基的“特异功能”:当他看到颜色,他觉得自己也同时听到了音乐。所以他说,“色彩是琴键,眼睛是琴锤,心灵则是钢琴的琴弦。而画家则是弹琴的手指,引发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在1984年被引进中国,虽然有着70多年的“时差”,但还是深刻地影响了国内“85美术新潮”运动,激发了当时的先锋艺术。 蓝色唤起人们对纯净和超脱的渴望,蓝色越浅,越淡漠。淡蓝色像一只长笛,蓝色犹如一把大提琴,深蓝色则像低音提琴;
蓝色唤起人们对纯净和超脱的渴望,蓝色越浅,越淡漠。淡蓝色像一只长笛,蓝色犹如一把大提琴,深蓝色则像低音提琴; 白色是一片毫无声息的静谧,像倏然打断旋律的停顿,但并不像死亡的沉寂,而是孕育着希望,犹如生命诞生之前的虚无……
白色是一片毫无声息的静谧,像倏然打断旋律的停顿,但并不像死亡的沉寂,而是孕育着希望,犹如生命诞生之前的虚无……
以音乐为灵感,康定斯基也常以《即兴》、《作曲》等类似乐曲名的方式来给自己的画作命名。仅以《即兴》为题的画作,就有三十五幅之多。
除了色彩之外,康定斯基还用音乐来诠释点、线、面。
“线”由点产生,更具方向性和张力,在旋律中,线条的粗细象征着音高的存在;
“面”是由两条水平线和两条垂直线框定的范围,水平线冷而静止,垂直线暖而静止,就像两个声部,决定了画面整体的音响。

 构图呈现在一个完美的方形上,围绕着两个明显的黑色对角线展开。在画面中央,一条笔直的对角线与另外一条曲折的对角线交错而过,线条穿过空间,并与其他色彩元素相互作用,将绘画的中心朝着画布的白色空间蔓延,而白色,被他视为音乐中的“深沉的寂静”。
构图呈现在一个完美的方形上,围绕着两个明显的黑色对角线展开。在画面中央,一条笔直的对角线与另外一条曲折的对角线交错而过,线条穿过空间,并与其他色彩元素相互作用,将绘画的中心朝着画布的白色空间蔓延,而白色,被他视为音乐中的“深沉的寂静”。 德国对俄国宣战后,俄国公民康定斯基被勒令三天内离开德国,他不得不返回俄国。
德国对俄国宣战后,俄国公民康定斯基被勒令三天内离开德国,他不得不返回俄国。
而德国恋人蒙特,也为了躲避战乱逃往瑞典。分别前,他们约定要在瑞典重逢。战后第二年,这对恋人团聚了3个月,他们商量着结婚事宜,在战乱中规划着未来生活。
这一时期,康定斯基没有画出一幅油画作品,只是画了些更具抽象风格的手稿和水彩画。 战后第三年,康定斯基邂逅了一位俄国上校的女儿——年仅23岁的妮娜,迅速与之闪婚。在阿赫特尔卡小镇消夏时,康定斯基醉心于新婚的喜悦,为了年轻的妻子,重新回到了具象绘画的创作。
战后第三年,康定斯基邂逅了一位俄国上校的女儿——年仅23岁的妮娜,迅速与之闪婚。在阿赫特尔卡小镇消夏时,康定斯基醉心于新婚的喜悦,为了年轻的妻子,重新回到了具象绘画的创作。 而在瑞典苦等着康定斯基的德国姑娘蒙特,一度以为康定斯基死于战争,或俄国的十月革命。
而在瑞典苦等着康定斯基的德国姑娘蒙特,一度以为康定斯基死于战争,或俄国的十月革命。
 一战结束后,蒙特回到德国,不久后,康定斯基应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邀请,携妻子妮娜一道去往德国。直到此时,蒙特才知道康定斯基背叛了自己,在极度失望和愤怒中,她拒绝归还康定斯基战前托她保存的作品。
一战结束后,蒙特回到德国,不久后,康定斯基应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邀请,携妻子妮娜一道去往德国。直到此时,蒙特才知道康定斯基背叛了自己,在极度失望和愤怒中,她拒绝归还康定斯基战前托她保存的作品。

1922年,康定斯基在包豪斯学院开启了长达11年的教学生涯,严谨的几何化风格逐渐突出,他用尺子、圆规,塑造出一幅幅三角形、正方形、圆形充斥的画作,并开始撰写他的第二本重要理论著作《点线面》,这一时期的主题,主要围绕着几何造型与色彩渐变。
平静的教授生涯,最终因为希特勒上台而告终,康定斯基流亡巴黎。
在巴黎的头几年,艰苦的生活并未阻挡他创作的热情,与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接触,让他的作品持续演进。经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介绍,他与妻子住进塞纳河畔的一套公寓。
这一时期,柔软的非几何轮廓生物和动物形态,明亮、绚烂的色彩充盈着他的画作。 《作曲IX》,整个画面被粉彩色和浓郁的色调铺满,构图围绕着彩色对角线展开。
《作曲IX》,整个画面被粉彩色和浓郁的色调铺满,构图围绕着彩色对角线展开。


不久后,二战爆发了,法国被纳粹占领。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非常不受待见,被纳粹称之为“堕落的艺术”,虽然彼时康定斯基的绘画已经受到美国的重视,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动荡的法国。
他和妻子妮娜几乎隐居了起来,物质匮乏,只能在纸本上作画。 1944年,康定斯基在巴黎病逝。
1944年,康定斯基在巴黎病逝。

下:生前使用的画笔、眼镜
以一战为界,恋人蒙特和妻子妮娜,分别保存着康定斯基战前、战后的主要作品。虽然经受背叛,蒙特在物质最匮乏的时期,也从未考虑出售康定斯基的任何一幅作品。
二战结束后,蒙特在80岁生日之际,决定捐赠出她妥善保管的400多件康定斯基画作,与昔日恋人一泯恩仇。
A:安格拉·兰佩(Angela Lampe),策展人、康定斯基研究学者
Q:这次展览基于康定斯基在不同城市的经历,分为五个部分展出,说说您的策展思路?
A:此次展览基于蓬皮杜中心丰富的馆藏,五个板块涵盖了艺术家从早年创作,走向抽象到成熟等不同阶段的作品。
“初始:技艺研习”,是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初习绘画的时期;“穆瑙:抽象的突破”,是他建立“蓝骑士”并转向抽象的时期;“俄罗斯:间奏岁月”,展出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返回祖国之后的创作;“包豪斯:理论年代”,是他最多产的时期;“巴黎:成熟时期”,则是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展出了康定斯基收藏的中国艺术杂志。另外,还有5尊中国古代青铜器与康定斯基的晚年画作一同展出。

A:康定斯基对东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艺术生涯的开端。当时他正为一家俄国杂志撰写关于慕尼黑生活的专栏。他提到了一次难忘的看展经历,其中关于日本和东亚的艺术品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这部分展览同时展出了日本艺术,及12世纪以来中国的绘画和雕塑。
在康定斯基的藏书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出版物。无论是在包豪斯时期,还是巴黎时期,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终不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尤为重视。

康定斯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物质匮乏,甚至只能在纸本上作画
Q:从您的理解,谈谈康定斯基艺术理论中的抽象画与音乐的关系?
A:康定斯基天生具有“联觉”能力,将听觉与视觉联系在一起,拥有“有色彩的听觉”。
在他的《论艺术的精神》中,他对色彩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并将不同颜色和不同乐器的音质进行了比较,比如,黄色相当于喇叭发出的高音,他还将这种联觉现象称为“不和谐”的美学。
A:整个展厅围绕一个中心部分展开,我们复原了康定斯基1922年为柏林“无评委艺术展”(Juryfreie)设计的门庭壁画,这是它首次在亚洲展出。此外,我们还展出了康定斯基在俄罗斯时期罕见的纸上作品,以及他在巴黎最后几年鲜为人知的生物形态绘画。
部分图片由西岸美术馆和蓬皮杜中心提供
原标题:《两任妻子捐出珍藏,我们才看到他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