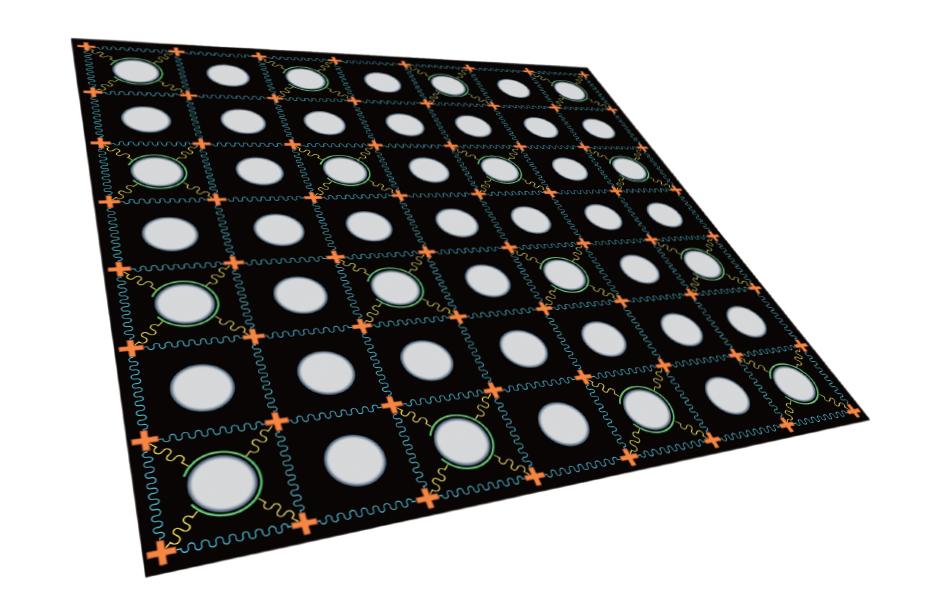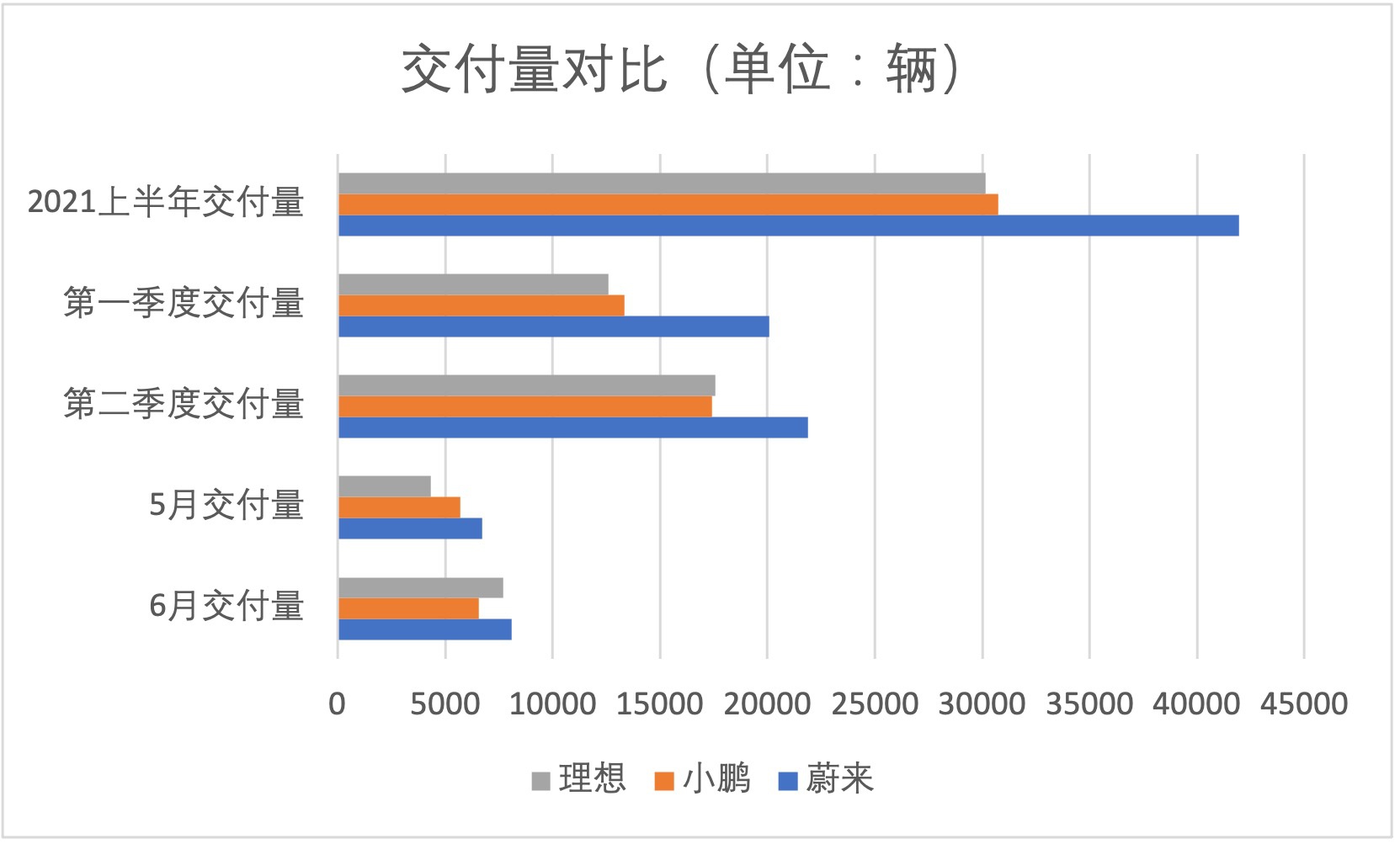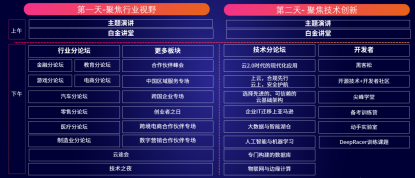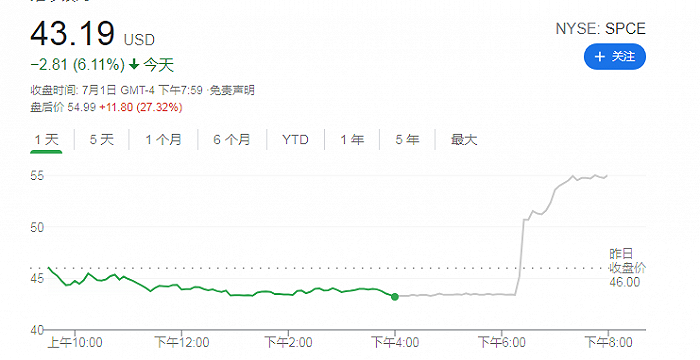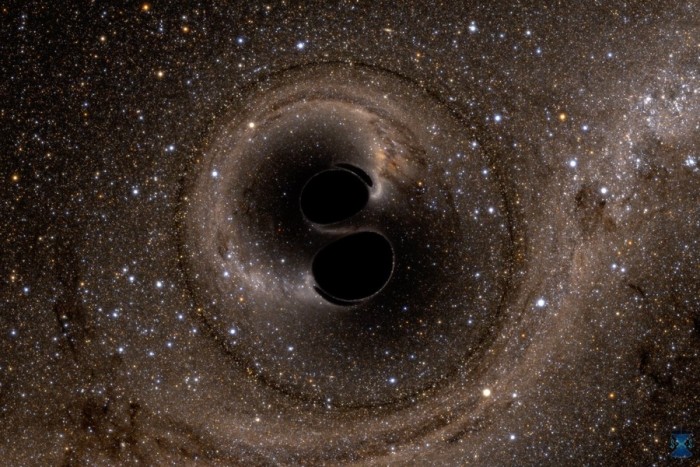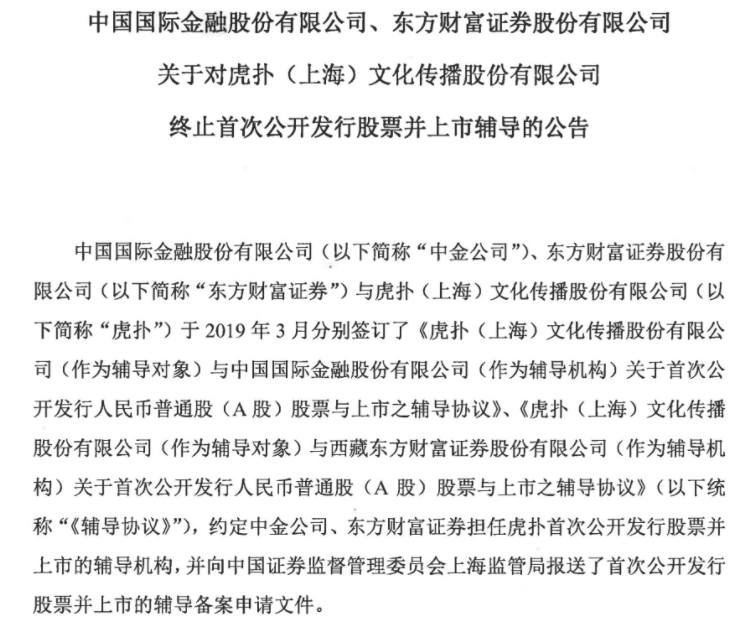原标题: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和阅读红色经典
“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到黄浦剧场看了《女篮5号》4K修复版。本来我以为老同志比较多,但那天下午却来了很多年轻人,电影演完后大家都还鼓掌了,我印象特别深刻。”6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上说道,“红色经典不仅是对五六十年代人的影响,也可能以某种形式活在我们当下的此刻。” 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
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思南读书会开办七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近四百余场活动。在这场迎七一特别讲座上,罗岗与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孙晓忠、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一同重拾对上世纪红色经典文学的回忆,分享红色经典在当下散发的活力和价值。
“十七年”文学是断层还是延续?
“教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定会涉及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无论是从文学史研究、教学还是从青年阅读来说,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罗岗谈道。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小说(1949~1966)的概括—,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与《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在这个时期,文学创作坚持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某种程度上“十七年”小说充当了社会生活教科书的任务。
虽然“十七年”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历经的一环,但由于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文学史讨论上争议颇大,甚至在许多中文系课堂中,该部分也会被压缩或简略处理。在19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必须要通过“新时期文学”才能加以证明。
不过罗岗提醒,文学史可能忽略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重要性 。他与孙晓忠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对他们来讲,教学研究和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不仅借助于文学史的叙述进入这段历史,而且红色经典也早已通过个人生命体验融进了他们的文化记忆里。
“红色经典的确是从小阅读时建立起的情感,我现在想自己为什么一直喜欢研究这一块内容,和我小时候的阅读习惯有关。”孙晓忠回忆道,“在1990年代我喜欢跑去华东师大后面的小摊子买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每个旧书的前面都盖着各种各样的单位公章,这是九十年代各个工厂图书室倒闭后流到民间的书,现在卖得很贵了。”
在孙晓忠看来,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和红色经典之间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逻辑联系。“虽然1980年代以后文学语境有了非常大地转变,但是共和国第一个30年书写创造出的成果仍然构成了整个20世纪的写作的前提,而且是重要的一份前提。”
实际上,新时期文学中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在跟之前30年的文学的遗产进行对话。张屏瑾认为,这种对话直到今天都还在展开。比如作家双雪涛在写作中就时常涉及父代与子代间的关系,父代正是处于建国的历史中。子代的成长仍受父代历史时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红色经典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史和写作意义延续上的重要性。 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现场。
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现场。重思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艺术性
从史学研究角度而言,回避某个特定时期的作品或许带来的是一部有缺憾的文学史。
孙晓忠认为,“十七年”文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段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业史》、《暴风骤雨》,无不于字里行间再现着那个时代中国特有的风貌,“20世纪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这些作品我感觉它们都是在做这样的探索”。
罗岗以从《荷马史诗》看希腊文化、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来类比,认为红色经典也就是在书写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史诗不仅仅是对于宏大事变的历史叙述,也包括对一个时代的民族的生存状况的记录,红色经典实际上是在非常自觉的做这种记录工作。”“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征,使得红色经典的价值应被重新得到评估。
对于红色经典作品,怎样理解、如何阅读、怎样接受,这其实就是在考虑它的艺术性的问题。红色经典历来被认为是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孙晓忠认为不然。
“比如说《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这一集,大家都喜欢。从文本角度,它是非常艺术的,而不能完全从革命或者阶级斗争的意义去框定它。”在孙晓忠看来,好的红色经典文学,不会只停留在阶级斗争式的口号上,而是懂得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将革命肉身化,将之落地,《红岩》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故事从江竹筠怎样变成江姐娓娓讲述,这是结合生活维度的艺术创造过程。“文学艺术在某种方面能凸显更强大的力量,通过某个人物把某种精神写出来,它可以将被之打动的人召唤进革命内部去,这是风格与修辞的力量。”孙晓忠说道。
红色经典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时”
近年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而言,红色经典又回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读这些作品。红色经典并没有落伍,而是以某种形式活在当下继续发展。
在课堂上,张屏瑾始终在寻找以当下话语激发青年学生重读红色经典的落脚点。讲到《青春之歌》,她觉得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学习目标、生活计划、理想追求,甚至对于爱情的选择,都与她的学生非常相似。在学习讨论《青春之歌》时,青年人自己就带有对这些问题的想法,甚至直接的个人体验,这种共情性往往为当代人进入红色经典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契机。
除此之外,罗岗认为,读《青春之歌》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这恰恰反映了对某些问题的探寻具有跨时代的连贯性。这具有一个探索的连贯性。而像80年代著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然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留存。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经典,经典能在当代发挥出什么样的价值,在罗岗看来,要将红色经典重新摆回历史语境中去探究,“读厚,了解历史语境;读薄,与今日对话。这样的话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双重呈现出来。”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刚诞生是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人物市井,语言低俗。从这个意义上经典是被人‘说’出来的,一辈一辈人的阅读接力,一代一代的体悟传颂。”孙晓忠认为,红色经典也同样如此,需要不断地被人阅读、不断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