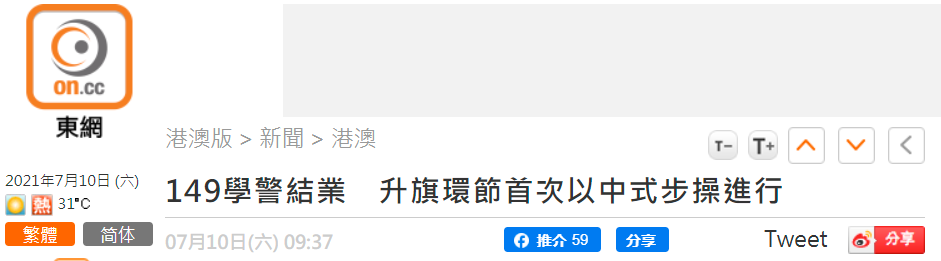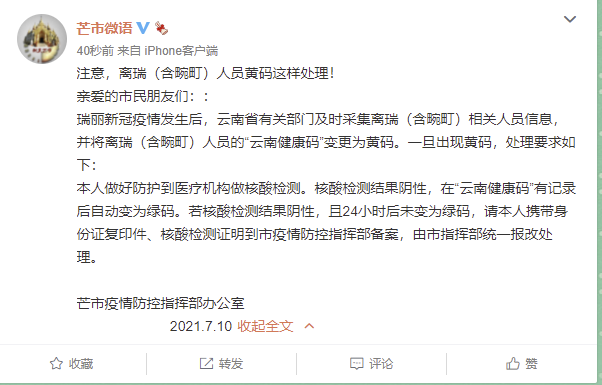原标题:叛逆的女孩与个人自由 | 重看小红帽、爱丽丝、睡美人
”我们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本书。“小红帽、爱丽丝和睡美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初读时,我们或痛恨于女巫的纺锤诅咒,再看时,迪士尼《沉睡魔咒》中的真爱之吻已经属于女巫而非王子。
童话故事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重读。加拿大文学家曼古埃尔在《迷人怪物》一书中亦再次走入了这些人物。在他的眼中,她们是被引诱的引诱者小红帽、用”语言“防身的爱丽丝,以及同无尽“时间”相联的睡美人。
# 小红帽 #
有些人物的名字体现了他们的肤色(白雪公主),有些体现了能力(超人)、体型(拇指姑娘),还有一些是他们的服装。一件血色的短斗篷定义了夏尔·佩罗在十七世纪晚期创作出的角色:一位热爱冒险的女孩。 她有一点纯真的味道,既有礼貌又有勇气,流露出微妙的吸引力,以至于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曾视其为初恋。“我觉得如果自己能与小红帽结婚,”他坦白道,“便会了解什么才是完美的幸福。”
她有一点纯真的味道,既有礼貌又有勇气,流露出微妙的吸引力,以至于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曾视其为初恋。“我觉得如果自己能与小红帽结婚,”他坦白道,“便会了解什么才是完美的幸福。”她的故事家喻户晓:母亲交给她的差事(为病中的外婆送去蛋糕和黄油),与狡猾野兽的会面(故事的关键所在),一路的各种干扰(捡橡子和追蝴蝶),外婆的悲惨命运(让人联想到约拿和杰佩托,她对冒牌货的盘问和异装狼的回答,恶魔的真面目最终揭晓(一种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教理问答)。
这则故事的前身其实隐匿在《散文埃达》之中,后者于十三世纪的冰岛写就。故事讲述了邪神洛基必须向巨人索列姆解释为何他的未婚妻(正是雷神索尔伪装的)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女性化。
“我从来没见过胃口这么大的新娘子。”在看到所谓的女士吞食了八条鲑鱼以及一整头牛之后,索列姆疑惑道。
“那是因为她太想见到你了,”洛基回答,“以至于八天都没吃任何东西。”
“为什么她的眼神这么恐怖?”索列姆注意到新娘面纱后那双锐利的雷电之眼。
“那也是因为她太想见到你了,”洛基再次答道,“以至于八晚都没有睡觉。” 漫威电影中的雷神索尔
漫威电影中的雷神索尔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各种颠倒角色: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女扮男装是很常见的——罗莎琳德、波西亚、伊莫金、薇奥拉——男扮女装也一样,福斯塔夫曾假扮成女仆福特的胖姨母。哈克贝利·费恩会穿得像小姑娘,自称莎拉或玛丽;罗切斯特先生会扮成年迈的吉卜赛占卜师;《柳林风声》里的蟾蜍会装作洗衣服的老妇人:他们都通过了有关身份质疑的教理问答。
小红帽的信条与梭罗一致:不服从。她知道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独裁式的要求,但具体如何全看她的心情。从一点到另一点间的直线不是她追求的路径,循规蹈矩也不是她的风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菲德会认同她。“我喜欢看到人们偏离正道,”他说道,“这才叫有趣。”因为小红帽偏离了正确的路径,所以她来到了森林,遇见了狼、伐木工,与奶奶一起历险。如果不是因为小红帽偏离了正道,故事便不会发生。
芝诺认为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如果想要从既定的地点来到下一个地点,我们必须到达两点之间的中点,而想要到达那样的中点,又必须到达起点和中点之间的中点,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小红帽证明芝诺的看法是错误的。运动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以下这些中点的存在:风景中熟透的浆果、丰盛的橡子、随手可摘的花朵。甚至狼的出现也仅仅是她与外婆家(她最终总会到达)之间的又一个中点罢了,因为这个叛逆的女孩(不听从母亲的规定,也不服从前苏格拉底的法则)是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她所停留的中点的。小红帽代表了个人的自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法国的革命象征玛丽安娜披着与她颜色一样的斗篷吧。 小红帽的故事在每个叙述者口中都稍有不同。在佩罗的笔下,她的结局是被狼吞食。之后的版本则更具同情心,引入了伐木工这个英雄,他在最后一刻出现,从狼嘴里救下女孩,又用类似剖腹产的方式救出了外婆。
小红帽的故事在每个叙述者口中都稍有不同。在佩罗的笔下,她的结局是被狼吞食。之后的版本则更具同情心,引入了伐木工这个英雄,他在最后一刻出现,从狼嘴里救下女孩,又用类似剖腹产的方式救出了外婆。佩罗没有描写小红帽与假外婆一起躺在床上的场景,但在故事结尾的寓意中写明了佩罗心中的狼的形象。“不是所有狼都是一样的,”他写道,“有的狼很狡猾,不会宣扬他们的意图,不易怒也不恶毒,谨慎自信又作风端正,跟随年轻女士的脚步来到她们的房前,甚至是床前。但是,当心!谁能想到这些说着甜言蜜语的狼才是所有狼中最危险的呢?”
狼的这种诡计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与佩罗同一时代的德舒瓦西神父就因其不知廉耻的行为而声名狼藉。他在回忆录中讲述道,他在童年时期就喜欢穿女性的衣服。异装后的他在布尔日度假时,遇到了一位佳隆夫人,对方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某天晚上,佳隆夫人提议让客人与自己的女儿睡同一张床。穿着褶边睡袍、头戴缎带睡帽的神父欣然同意。没过一会儿,女孩大喊出声:“哎呀!真舒服!”“孩子,你还没睡吗?”听到声音的母亲询问道。“我只是刚上床的时候有点冷,”女孩机智地反应道,“但现在我暖和了,非常非常满足。”
这便是这位神父的恶作剧,而百年后,萨德侯爵也发现小红帽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为了逮到他的猎物,狼会不择手段。”这是他在查伦顿疯人院的病房中写下的警言。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无论小红帽怎么做,最终都会躺在狼的床上,她仍然有两个办法逃脱。一是适应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即萨德的《瑞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的主旨),二是成为自己命运的情妇(也就是萨德的《于丽埃特,或喻邪恶的喜乐》所说的)。 这两种方法都为后人所运用。前者的例子有大仲马的茶花女、加尔多斯的玛丽亚奈拉、狄更斯的小杜丽,后者则有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巴尔加斯·略萨的坏女孩。而小红帽则两者兼具。被引诱的引诱者,世俗又天真,她在林中漫步,自由自在,不惧虚伪的狼。
这两种方法都为后人所运用。前者的例子有大仲马的茶花女、加尔多斯的玛丽亚奈拉、狄更斯的小杜丽,后者则有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巴尔加斯·略萨的坏女孩。而小红帽则两者兼具。被引诱的引诱者,世俗又天真,她在林中漫步,自由自在,不惧虚伪的狼。# 爱丽丝 #
在照亮我们文学史的所有奇迹中,没有多少人物比爱丽丝更加耀眼。1862年7月4日下午,牧师查尔斯·路特维希·道奇森(CharlesLutwidge Dodgson)在友人的陪伴下带着基督教堂学院院长利德尔博士的三个小女儿在牛津附近共游泰晤士河,船程三英里。女孩们想听故事,道奇森牧师便以他最喜欢的朋友——七岁的爱丽丝为主角即兴创作了一个。
“有时候为了逗我们,”爱丽丝·利德尔(Alice Liddell)多年后回忆道,“道奇森先生会突然停下,然后说:‘且听下回分解。’接着我们三个会大喊:‘啊!但现在就是下一回!’再劝他半天,故事又会重新开始。”回程后,爱丽丝拜托道奇森为她写下这个故事。他答应尝试,最后几乎通宵完成手稿,并起名为《爱丽丝的地下世界探险记》。三年后,也就是1865年,这则故事由伦敦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作者的笔名为“刘易斯·卡罗尔”,书名改为《爱丽丝梦游仙境》。 爱丽丝的探险故事是在一段行进的旅途中完成的,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爱丽丝的坠落和探索,她的遭遇与发现,那些三段论、双关语还有机智的玩笑话,所有奇妙而连贯的剧情发展都是当场讲述出来的,这本身就像是一种奇迹。不过,没有奇迹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也许爱丽丝故事的根基比其诞生的背景更加深远。
爱丽丝的探险故事是在一段行进的旅途中完成的,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爱丽丝的坠落和探索,她的遭遇与发现,那些三段论、双关语还有机智的玩笑话,所有奇妙而连贯的剧情发展都是当场讲述出来的,这本身就像是一种奇迹。不过,没有奇迹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也许爱丽丝故事的根基比其诞生的背景更加深远。我们不会像阅读一般的儿童文学那样看待爱丽丝系列故事。其中的地理信息与某些神秘地点(比如乌托邦或阿卡迪亚)一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在《神曲》里,炼狱山顶上的守护神向但丁解释道,诗人吟诵的黄金时代是失乐园的潜意识记忆,是完美幸福的消失状态。那么仙境也许就是完美理性的潜意识记忆,而这种状态在传统社会文化的眼中却是极度的疯狂。
任何跟随爱丽丝掉入兔子洞、走过红皇后的迷宫王国、穿越镜子的人都不会是第一次这么做。只有利德尔姐妹可以说是见证了创造的过程,但即便是那时,她们也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自那一天起,仙境和象棋王国便进入了所有的图书馆,就像伊甸园一样,无需涉足也能确定它的存在。爱丽丝去过的地方是我们梦想人生中不断重现的风景(虽然它们不在任何地图上。梅尔维尔说过,“真实的地点都不在地图上”)。 因为爱丽丝的世界无疑就是我们的世界:不是抽象的象征语汇,不是精心策划的寓言,也不是反乌托邦的传说。仙境就是我们每天得以找到自我的疯狂场所,照例有天堂、地狱、炼狱,是漫游在生活之中的我们必须漫游的地方。
因为爱丽丝的世界无疑就是我们的世界:不是抽象的象征语汇,不是精心策划的寓言,也不是反乌托邦的传说。仙境就是我们每天得以找到自我的疯狂场所,照例有天堂、地狱、炼狱,是漫游在生活之中的我们必须漫游的地方。爱丽丝(与我们一样)全程只有一件武器防身:语言。是语言让我们穿过了柴郡猫的森林和红心王后的槌球场。是语言让爱丽丝发现事物本质与表面的不同之处。是她提出的问题让疯狂的仙境浮现,而在我们的世界里,仙境却被隐藏在保守传统的薄衣之下。
我们可能会试着在疯狂中找寻逻辑,就像公爵夫人那样借万事总结出教义,无论多么荒谬,但事实就像柴郡猫对爱丽丝所说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不管我们走哪一条路,都会发现自己身处疯狂的人群中,而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用语言紧紧抓住我们视为理智的东西。言词向爱丽丝(以及我们)揭示了这个迷惑世界唯一不争的事实,那便是在表面的理性之下我们都是疯子。
我们会像爱丽丝那样,流下的眼泪差点把自己和其他人淹死。我们会像渡渡鸟那样认为无论我们朝哪个方向奔跑,无论跑得多慢,我们都是赢家,都应该获得奖赏。我们会像白兔先生那样处处发号施令,仿佛他人理应(且有幸)为我们服务。我们会像毛毛虫那样质疑同伴的身份,却对自己一无所知,甚至即将失去自我。我们会像公爵夫人那样坚信年轻人的恼人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对行为背后的原因毫无兴趣。我们会像疯帽子那样觉得只有自己有权享受长桌上多人份的美食,我们讽刺地为饥渴的人们提供酒水,其实除了今天,没有一天有红酒和果酱。 同样身为远行者的我们在爱丽丝的旅途中发现了自己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主题:追求梦想却又失去,随之而来的泪水与痛苦,为了生存而竞争,被迫任人差遣,迷失自我的梦魇,家庭破裂带来的影响,屈服于荒谬的仲裁,权力的滥用,误导性的教学,对逃脱惩罚的罪行与不公正的惩罚缺乏了解,以及长期以来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以上一切,再加上无所不在的疯狂氛围,就是爱丽丝系列故事的梗概。“若要定义真实的疯狂,”《哈姆雷特》中写道,“除了疯狂还能是什么?”爱丽丝会表示赞同:疯狂就是将一切不疯狂的事物排除在外,因此仙境中的所有人都符合柴郡猫的名言。但爱丽丝不是哈姆雷特。她的梦不是噩梦,她从不自怨自艾,不会自视为冥冥之中的正义之手,绝不执着于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坚信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同样身为远行者的我们在爱丽丝的旅途中发现了自己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主题:追求梦想却又失去,随之而来的泪水与痛苦,为了生存而竞争,被迫任人差遣,迷失自我的梦魇,家庭破裂带来的影响,屈服于荒谬的仲裁,权力的滥用,误导性的教学,对逃脱惩罚的罪行与不公正的惩罚缺乏了解,以及长期以来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以上一切,再加上无所不在的疯狂氛围,就是爱丽丝系列故事的梗概。“若要定义真实的疯狂,”《哈姆雷特》中写道,“除了疯狂还能是什么?”爱丽丝会表示赞同:疯狂就是将一切不疯狂的事物排除在外,因此仙境中的所有人都符合柴郡猫的名言。但爱丽丝不是哈姆雷特。她的梦不是噩梦,她从不自怨自艾,不会自视为冥冥之中的正义之手,绝不执着于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坚信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语言对爱丽丝来说并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活物,而思考不会改善也不会恶化事物。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身躯融化,也不希望它膨胀或收缩(尽管为了穿过狭小的花园门口,她会许愿自己能“像个望远镜里的小人”)。
语言对爱丽丝来说并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活物,而思考不会改善也不会恶化事物。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身躯融化,也不希望它膨胀或收缩(尽管为了穿过狭小的花园门口,她会许愿自己能“像个望远镜里的小人”)。她绝不会丧命于有毒的刀刃或像哈姆雷特的母亲一样饮下毒酒:当她拿起写有“喝掉我”的瓶子时,会首先查看瓶身有无毒药的标记,“因为她听说过很多难忘的小故事,孩子被烧伤,被野兽吃掉,还有其他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同伴的教训”。爱丽丝比丹麦王子更具理性。
不过,挤在白兔先生的房间里动弹不得的爱丽丝一定也像哈姆雷特一样想象过,如果自己不是被束缚在果壳之中,而是注定成为无限宇宙的国王(或女王),那么她的态度将不仅仅是从容不迫:她会努力争取,比如在《镜中奇遇记》里赢得梦中的皇冠。爱丽丝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严格的维多利亚式戒律,而非宽松的伊丽莎白式准则,她相信的是原则与传统,不会在抱怨和拖延上浪费时间。
在她的旅程中,爱丽丝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一样,以简单的逻辑去面对不理智的行为。常规(现实的人为构造)与幻想(自然存在的现实)相悖。爱丽丝自知逻辑是我们将意义赋予胡言乱语并揭示其秘密法则的方法,她毫不留情地加以运用,包括在长辈和上级面前,无论是面对公爵夫人还是疯帽子。
如果争论失去意义,她仍会坚持证明现状的不公与荒谬不言而喻。当红心王后要求法庭“先判刑——再裁决”时,爱丽丝立刻反驳道:“胡说八道!”我们世界里的大多数谬论都只配得到这样的反驳。 虽然我们的世界就像仙境一样有着明显的疯狂之处,但也隐隐约约透露出某种意义,而如果我们尽力看透那些“胡说八道”,会发现一切都能得到解释。爱丽丝的冒险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精确度和连贯性,所以作为读者的我们会越发觉得这些毫无意义的事物难以理解。
虽然我们的世界就像仙境一样有着明显的疯狂之处,但也隐隐约约透露出某种意义,而如果我们尽力看透那些“胡说八道”,会发现一切都能得到解释。爱丽丝的冒险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精确度和连贯性,所以作为读者的我们会越发觉得这些毫无意义的事物难以理解。整部小说就像是禅宗心印或是古希腊的悖论,意义深刻却又令人费解,游离在启示的边缘。我们跟随爱丽丝掉入兔子洞,与她一同踏上旅途,会发现仙境的疯狂并不随意任性,也不纯真无邪。
刘易斯·卡罗尔的创作一半是史诗一半是梦境,在僵硬的土地与奇幻的境界之间为我们打造了一处必要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有利的地点以几近透彻的眼光观察整个宇宙,原原本本地将之转化成一段故事。与令道奇森牧师着迷的数学公式一样,爱丽丝的探险既是确凿的事实,也是崇高的创造。它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方面让我们立足于现实,另一方面让我们重新思考甚至改变现实。就像是栖息在枝头的柴郡猫,在迷惑人心的可见物与不可思议(又令人安心)的一缕微笑之间飘忽不定。
# 睡美人 #
她的故事与时间有关:浪费的时间,拖延的时间,等待、做梦、无知的时间。故事的开头就不美好。睡美人在出生时收到了所有仙女的祝福,只除了一位国王忘记邀请的仙女,后者因此对她施下咒语,诅咒她在未来被有毒的纺锤刺中而死。
无论是皇室法令还是善良仙女的魔法都无法消除这份恶意,无论是禁止使用纺锤还是将死亡的长眠改变为永无止境的睡梦都无法阻挡这可怕的诅咒。大人们想尽各种办法依旧是徒劳,女孩长大成人,触到了纺锤,陷入沉睡。与此同时,整座城堡也陷入了沉睡,等待着真爱之吻在某一天唤醒一切(希望如此)。美人入睡,时间停止。 有几位作家的故事与睡美人的叙事意图类似:将曾经鲜活的世界以静止的状态封存在尘土飞扬的城堡或被掩埋的庞贝古城中。比如华盛顿·欧文所作的瑞普·凡·温克尔的故事。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寺院,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雪的伪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伯特伦旅馆之谜》。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参与倾茶事件的美国州府,它们如今可能会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找到暗藏的共鸣——我们往往难以区分沉睡与死亡。
有几位作家的故事与睡美人的叙事意图类似:将曾经鲜活的世界以静止的状态封存在尘土飞扬的城堡或被掩埋的庞贝古城中。比如华盛顿·欧文所作的瑞普·凡·温克尔的故事。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寺院,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雪的伪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伯特伦旅馆之谜》。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参与倾茶事件的美国州府,它们如今可能会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找到暗藏的共鸣——我们往往难以区分沉睡与死亡。沉睡中的美人,这便是她吸引王子的地方吗?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一言不发,双眼紧闭,无知无觉也毫无抵抗能力?青年时期的巴勃罗·聂鲁达将这种古老的男性幻想用简单的诗句写在了他的二十首情诗之一中:
我喜欢你安静的样子,因为你仿佛并不存在,
你听见我在远方的声音,它却无法抵达,
你的眼睛仿佛已经飞走,离我而去,
你的双唇仿佛被吻封缄。
埃德加·爱伦·坡则直言不讳。他在《写作的哲学》(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写道,已逝的美丽女性“无疑是这世上最具诗意的主题”。毕竟你无法比死亡更沉默。 死亡与沉睡早已融合在文学之中。在四千多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诗人便将沉睡称为死亡的兄弟,这一可怖或可叹的定义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在死亡的长眠中,时间是停止的,即圣安塞姆所说的天堂的状态。而在尘世的夜晚,时光在流逝,做梦的人被迫等待他们得以醒来的那一刻。
死亡与沉睡早已融合在文学之中。在四千多年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诗人便将沉睡称为死亡的兄弟,这一可怖或可叹的定义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在死亡的长眠中,时间是停止的,即圣安塞姆所说的天堂的状态。而在尘世的夜晚,时光在流逝,做梦的人被迫等待他们得以醒来的那一刻。智者阿方索在其制定的《七编法》中提到过一位僧侣,他想知道天堂里的时间是如何运转的。某天早晨,他听见窗外有鸟鸣声,遂走进花园深处一探究竟,这时候他的耳边传来一句低语:“这便是天上的一秒钟。”大喜过望的他回到房间,发现自己的师兄弟早已死去,那鸟鸣的一瞬间,是尘世间的三万年。
按照神学家的说法,天堂的时间没有长度,因为每一时刻都献上了那里所能拥有的一切。而在地狱,时间是永续的,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希望,什么事情都无法发生,除了无望的等待。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回忆道,他的一位叔叔曾在街上拦下他,问他:“你知道上帝是怎么折磨罪人的吗?”荣格摇摇头。“他让他们等待。”叔叔说完便离开了。
沉睡中的美人是身处天堂还是地狱呢?既然城堡中的时间停滞不前,那么我们会认为答案是前者;然而她的沉睡又是一场无尽的等待,这意味着答案应该是后者。
如果她身处天堂,那她永远也不会苏醒,因为苏醒将破坏存续的现状,这种美好现状下的公主是永远美丽、永远纯真的,永远被身穿蓝色礼服的王子渴望着。
而如果她身处地狱,那么睡美人便是在她丧失纯真前的那一刻陷入睡眠的,因为如果王子前来唤醒她,会将她困在时间的枷锁上,迫使她在一瞬间找回外部世界流逝的岁月。 睡美人会苏醒过来,但她的皮肤也会瞬间起皱,视线变得暗淡,珍珠白的牙齿掉落,金色的头发花白,受到惊吓的王子会是她孙子般的年纪,甚至是曾孙子也说不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结局都不会是幸福的。
睡美人会苏醒过来,但她的皮肤也会瞬间起皱,视线变得暗淡,珍珠白的牙齿掉落,金色的头发花白,受到惊吓的王子会是她孙子般的年纪,甚至是曾孙子也说不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结局都不会是幸福的。或许这才是那位被国王遗忘的仙女所下的诅咒:不能优雅地老去,不能拥有循序渐进的智慧,不能享受四季的轮回与变换;只能与整形手术、肉毒杆菌、乳房填充、猴腺血清绑定(如果她还想成为王子眼中的睡美人的话)。
不过,她也有别的选择。她可以拒绝诅咒,拒绝祝福,拒绝沉睡的侍从,拒绝父母的失礼行为,拒绝一位又一位王子。她可以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卡门·拉福雷特笔下的安德烈娅——两位现代版睡美人一样,狠狠关上魔法城堡的大门,睁大双眼直面这个世界。
本文节选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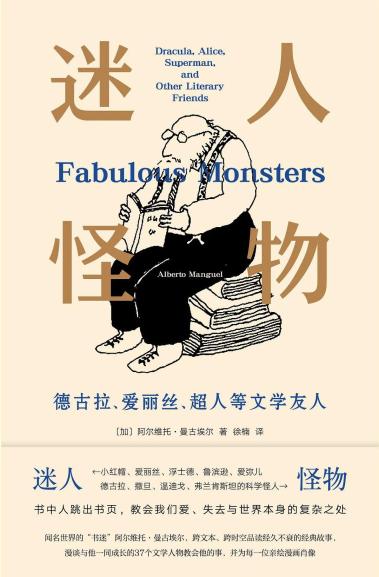 《迷人怪物》
《迷人怪物》作者: [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