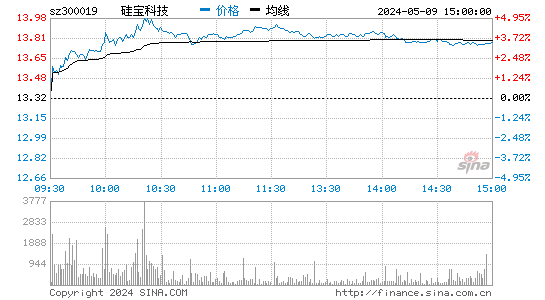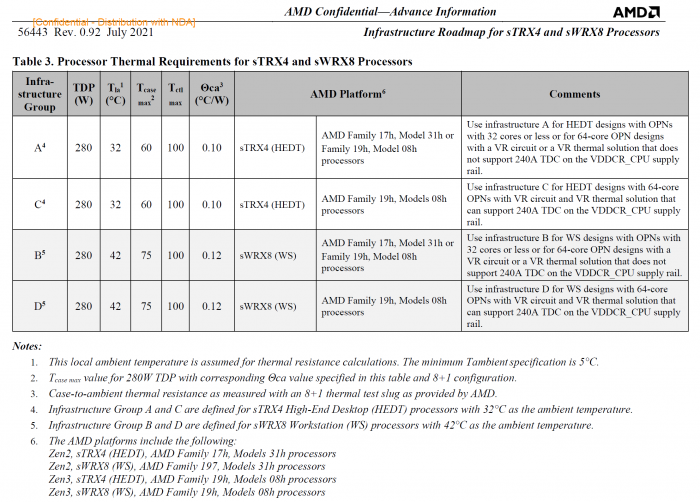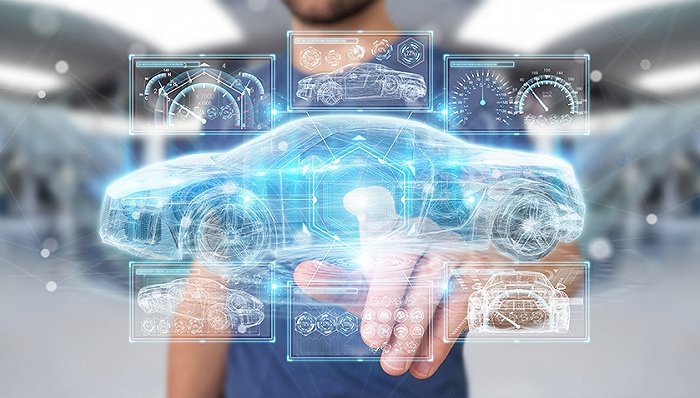原标题:专访|作家陈言:我只是如实去写被生活淹没的人
莆田,地处福建中部,近些年,因为种种负面新闻而被公众记忆。但在作家陈言的笔下,莆田得以穿越现代传播的迷雾,展露真实温润的日常。
1980年出生的闽籍作家陈言,十多年来一直在莆田默默写作。在不断遭遇退稿中,一度怀疑自己的写作才能。2017年,《上海文学》4月号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静瑜》,这让陈言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近日,他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蚂蚁是什么时候来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对其进行了专访。

《蚂蚁是什么时候来的》(以下简称《蚂蚁》)收录十个短篇和一个中篇,陈言以缓慢而饱蘸深意的笔端带领读者进入南方沿海以莆田周边为代表的乡镇生活,以小说的体例贡献了一部21世纪的闽中地方风物志。
更为迷人的是作者笔下福建沿海小镇那些普通人具体而微的生活和彷徨——他们困惑地彷徨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无望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出路。正如评论家张定浩所言,“陈言如实地去写被生活淹没的人,写那些在某个角落里静静毁坏掉的生命。”
阅读陈言,能够感受到一种鲜明的南方叙事:安静,温润,如电影长镜头一般缓慢,沉默的乡镇和沉默的事物借助作者饱蘸深意的笔端说话。对于陈言来说,写作同样也是一种发声,一种劳动,一种争取尊严与自由的方式。十几年来,他孤独而勤奋地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蚂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必须进入状态。就像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必须很快进入状态,否则那飞机就要在短短跑道的尽头掉入海里。”
对话
这是你出版的首部小说集,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言:这本小说集的出版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它让我的整个生命的感受力似乎一下子打开了,也让我面对困难的勇气显得更足一点。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写了很多年,不断遭遇退稿,有段时间很绝望,怀疑我自己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的朋友张定浩把小说《静瑜》推荐给《上海文学》小说编辑崔欣,说请她看看。崔欣很快就来信,表扬了这篇小说,还说想了解我的写作情况。这篇小说是一年之后才在《上海文学》刊发的,崔欣通知我小说发表的时候,那时还是借调上班处境微妙的我激动得穿上运动服,在荔枝林带跑了一圈又一圈,脑子里不断地散发着一种奇妙的沙沙声,那是关于那篇小说最美好的记忆。隔了一年之后,崔欣又发了我的一个短篇《贵客》。崔欣这两次对我的鼓励特别重要,她让我看到了自己写作的可能,也珍视了这种可能,不至于庸碌、颓败。
《蚂蚁》中大都是你熟悉的人和事物,在多大程度上能看到你个人的影子?
陈言:
我的小说确实有不少我的影子,有时在日常细节处理上也有意无意地留下个人的痕迹,但我不认为那个就是“真”的自己,更多是在心理体验上的相似,甚至可能是对“真我”的一次反叛。我的小说即便是有原型进入写作之后也是一个综合变化之后的人物,这个人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努力要去调动我个人的经验,传递我个人感受,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你通常是如何去把握笔下的人物?
陈言:
沈从文说要贴着人物写,如今这基本上变成写作上的信条。难度在于贴着人物,首先得要了解人物,包括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等,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世界生活。忽略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内心生活,你很难写好这个人物。当然,最难的其实还是你为何选择这个人物而不是选择那个人物,这个人物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的,特别是只有这个人物才能调动你的全部经验和神经。这里不仅涉及写作的训练、经验和对文本的追求,更涉及到你对生活的理解,你对人与事的态度。
崔欣说你的小说“是南方雨季的一次漫步,温润,从容,水汽氤氲。”张定浩说,“透着一种少有的室息感。”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说“读起来仿佛窒息地行走水中,迟缓、滞重、犹疑,但付出耐心之后,人的感官在衰弱中反而变得空明、智慧。”你如何看待这些评价?你的文风是如何形成的?
陈言:
谢谢推荐者的赞誉和勉励。就文本来说,这可能跟我的相对内向的性格有关,也与最初的阅读兴趣有关。我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安静,我喜欢安静地想一些事,这样我就和那些姿态和语调都比较低的作品有深切的心灵感应,比如我读到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奥兹的《了解女人》《莫称之为夜晚》,奈保尔的《抵达之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当然,这种叙述笔调和我的笔下人物的气息是一定要吻合的,就像我们摸自己的脸,疼自己的痛,要是离开这种合理性的话,就会显得别扭。
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比较偏爱内心叙事?
陈言:
是的,我觉得这是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我记得2007年底到2008年初,我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七卷本,这次阅读的经验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叙述方式。后来,我又系统地看了川端康成、库切、奈保尔、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等这些注重内心叙述的作家的作品。当然,我觉得这还不仅仅是叙事方式问题,更是一种看待世界方式。这些我喜欢的大师们彻底转变了我原先看待世界的方式,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那段学徒期中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直到这种叙述方式和我要写的世界对应上了。其实,当你拥有看待世界的方式,你就会拥有进入笔下人物内心的一种方式。人物拥有了内心,小说才真正拥有了可信度。
《蚂蚁》似乎没有特别激烈的矛盾冲突。你是如何处理日常性和故事性的?
陈言
:如同我们这种日常化的世界一样,小说中的日常化一定程度上是对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追求,而且小说写作的难度恰恰也在于对日常化生活的态度上。因为有了日常化,你的故事性才有了可靠的一面,否则那个故事只是为了完成编造的任务,完成所谓的创作理论,达到可读性的效果。相反,在好的作品中,故事性和日常化是相互作用的,这让我想到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和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他们的电影镜头都是日常化的,其实那种日常化也是精心挑选的,是为了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而故事的发展就是为了呈现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可能呈现社会的形态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反思等等。如果不能达到呈现这些的话,那么故事性就变得单薄甚至造作。
确实,是枝裕和、李沧东叙事中的暗流,可能比某些动作片还要汹涌。
陈言:
是的。小说肯定需要一个故事,只是不同的人理解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有些故事在你看来是有意思的故事,可是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些老套陈旧的东西,相反,有些日常化的细节,在另一些人看来藏着很深的故事,一个“一唱三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觉得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中的镜头细节可能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或者说那就是导演真正要传达的故事,也是真正感染观众的魅力所在。日常细节其实是最难把握的,因为细节,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人进而理解一个人甚至怜悯一个人和他的世界。我这里所说的细节其实不仅是动作、语言、神态,还包括外在的景物、光线、温度、纹理等等,正是这些共同构成我们对故事的理解。
今天的整个故事文本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很容易被一般人忽略掉,我的意思是现在的故事文本可能需要有耐心的读者,需要懂得捕捉细节的人,需要可以对话的人,甚至一起参与文本的人,否则那些了不起的“发现”很容易就在快速阅读中滑过,正是这种阅读习惯会导致阅读类似库切这样的作家会轻易下结论以为库切只写了“性”,以为《安娜·卡列宁娜》只是写了三角恋,以为《包法利夫人》写的不过是一个出轨的女人的故事,以为奈保尔的《抵达之谜》只是散文化的自言自语的碎片组合。
澎湃新闻
:在这种背景下,当下进行小说创作的难点在哪里?
陈言:
小说最难的是认识一个个人物,既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又跳出这生活的逻辑来创造这些人物,来勘探我们的时代,进而探寻生命的意义和表达一种美学。人们常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要达到诗的高度。这话有时听起来可能很虚,但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短篇小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要有“发现”。要发现点东西对大多数作家来说都是困难的,更何况是在这么有限的文字空间。我甚至觉得更大的难度恰恰在于这有限的文字,要产生“无限”的感觉。
中篇呢?
陈言:
有时在一些作家笔下短篇和中篇区分度并不大,同样,在他们笔下中篇和长篇也区分度不大。他们如此区分很多时候是因为素材处理的需要,就比如门罗的短篇和中篇,比如多丽丝·莱辛的中篇和长篇。实际上,在那些了不起的作家那里,他们考虑的始终是人物和他们的世界(包括内心生活),文本的长短很多时候都会被他们忽略掉,恰恰相反,那些过于考究文本的作家很多时候显得不那么放松,甚至有些进入职业化编造小说的歧途。
张定浩说你“如实地去写被生活淹没的人,写那些在某个角落里静静毁坏掉的生命”,应该如何理解“被生活淹没的人”?
陈言:
张定浩的这段评价于我不仅是褒奖更是一种巨大的鞭策。我所写的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自身也是卑微的个体,也是我们小说中的一个或安静或不安的人物,我们是跟他们,我们自己的另外一面镜子,零距离连在一起。只要一落笔,我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整体的感觉,我知道一年四季耕作的情况,知道自己也是他们困境中的一个,也是那个困顿、卑微、委屈者和失败者。
澎湃新闻
:奥康纳说到契诃夫短篇小说时,也说到他的艺术里充斥着“新的被淹没的人群”。把这些人的声音打捞起来,是不是也是你的写作方向?
陈言
:你说得太好了。每个写作的人都在努力打捞起即将消失的人或声音。赫塔·米勒说得更让人震撼,她说写作就是带着收拾遗物的心情,而《追忆逝水年华》简直就是普鲁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长信。
你提到了很多名字,有没有种大师情结?
陈言:
名单还会更长,这些都是我和身边朋友整天谈论的作家。是的,我们没有别的老师,只能以大师为师。在小地方写作,必须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人家写六分,你就得写七分、八分。不然人家不会注意到你。
你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