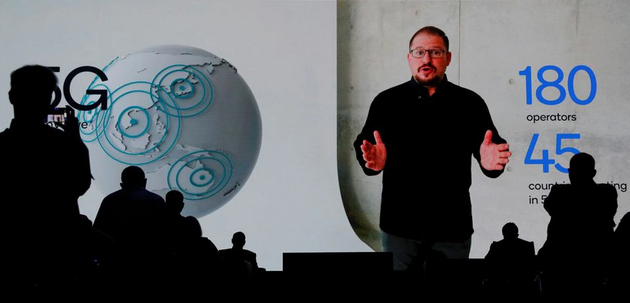原标题: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上):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
【主持人语】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已快2年,科学技术在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显,但为抗疫所采用的诸种技术治理措施也引发不少争议和担忧。这引起了专门研究科技问题的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来自中国、美国和德国的3位技术哲学家对全球疫情技术治理展开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论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发表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2021年第1期上。
[电子版参见: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
他们的观点受到国际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关注,9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技术哲学家发表了针对性的意见。整组笔谈以英文和德文发表于德国的《技术哲学年鉴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编,德国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为国际技术哲学界声誉卓著的资深学者,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与疫情应对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于新冠疫情反思颇具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组笔谈。整组10篇文章现分为上、中、下三篇,本文为上篇,包括来自中、美、德的3位技术哲学家合作的《新冠视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与三篇回应《人口与生命系统,或:曲线与直线》《管控与试验间的紧张地带:“精细化技术治理”的轮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新冠疫情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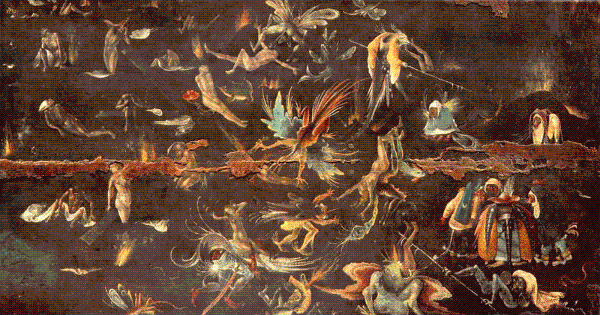 新冠视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
新冠视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作者简介: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与公共政策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研究。阿尔弗瑞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德国达姆施达特工业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STS研究。彭家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在欧洲和北美,新冠疫情有时被人称为一场压力测试(stress-test),而在中国,则被喻为一面“照妖镜”,贤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这场疫情是对公众、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挑战,许多问题和特征都在其中被揭示出来。我们居住在社会-技术世界或技术圈(technosphere)中的方式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来自不同国家的3位技术哲学家,曾相聚于地处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通过收集显著的观察结果,在此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表明技术哲学与理解新冠疫情(SARS-CoV-2、COVID-19)及其各种应对之策的相关性。
[1]
虽然比较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但我们的目标不是确定其异同。公开的政治叙事已经广为人知,与记者、政治理论家和舆论领袖密切相关。在这些叙事中,解释规则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德国效率,以及美国的混乱和暴力状态。当叙事转向需要流行病学应对的一种技术挑战时,解释规则发生改变。由此视之,在不同国家看到的其实是同一类型行动的变体——相似的困境和调整,但得到不尽相同的应对。当技术管理(technical management)问题被放在第一位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如何协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在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全部含义。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治理理论的词汇不足以打开社会约束(Sachzwang)或技术迫切性(technical exigency)的“黑箱”。关于此次疫情的技术性和技术治理层面,当凝视全球范围内瘟疫这面照妖镜时,我们希望像哲学家那样追求一种自我理解。
1. 公众讨论的主要基调反映出一种技术上的、也许是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据此,“新冠危机”是以技术和管理的术语来定义的。它要求对病毒和“指数级传播的逻辑”(logic of exponential spreading)做出有效的反应——如何使曲线变平,如何追踪和打破传染链,如何保持经济运行,如何调整医疗健康系统的能力。
2.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通常强调文化传统和公共价值观的差异,因为这是他们常用的分析框架。作为技术哲学家,我们从技术行动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形势——看到社会努力应对疫情管控的重大实际问题,同时屈服、挣扎——甚至对抗——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
3. 无论是微妙颠覆,还是暴力对抗,对需要做什么以及对替代办法的任何讨论,都代表着语域的转移,这超出保护大众免受病毒不受控制的传播之威胁的技术简单性(the technical brief)的范围。
4. 我们确定了三种技术范式或方式。“大方案优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通过国家官僚机构以及19世纪的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唤起数字治理的程序。它将政治体的所有成员视为风险承担节点,它们的系统交互需要统一管理。而“拼凑满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则利用许多不同来源的流行知识,这些知识不提供全面控制方法,但它们冗余地共同工作,以显著降低感染风险。因此,“拼凑满足”类似于公民科学(Bürgerwissenschaft)。第三种范式是“实时响应”(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到处都是地方性分布的监测和管理,如消防部门那样开发和部署知识和工具——一旦发生疫情,“火灾”将被扑灭,传染链将通过“实时响应”而被切断。虽然这些技术范式相互竞争,但没有被公开讨论。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有在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政策调整和各种行为者之间的责任转移时才能显现出来。
5. 这三种方式对应处理不确定性的三种实践态度。许多人更倾向于谨慎的一面,采取严格的风险规避策略(“大方案优化”),其他人愿意冒险,因为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围内(“拼凑满足”),而其他人则在一个实时反馈循环中修改他们的风险行为,该循环不断地评估所采取的措施和当前趋势(“实时响应”)。应对“新冠危机”技术框架的另一种“方法”是否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真实性,人们可能会把这称为某种形式的“缺陷”——远离那些看到问题的人,从而在某些情况下远离社会主流。
6.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
[2]
、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
7. 常见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术被另眼看待,受制于各种不同技术方法的调整。它们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复。同时,它们象征着效率,代表着团结、默许或共谋,而被用于在“抗击疫情”的国家工程中。相反,卫生消毒技术以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方式实施,其基础似乎是赋予每个人以权力的公共卫生习惯。各种统计和控制技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这些技术仅为预先确定的技术目标提供信息和交流。
8.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圈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技术圈在进化和逐渐变化。它可以是我们协调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生活形式。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它可以颠覆既定的生活形式。正式任命、合同盖章以及做出承诺,以往人们都要握手,现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触或礼貌的鞠躬所取代。家庭生活和邻里互动不再是围绕着“看见”(see),而是围绕着避开对方来重新组织。进入公共场合,人们不再期望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脸。与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经历一样,这些都不是反映新观点或新信仰的微小调整,而是深刻地重构人类关系。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性不是过去的样子。在新冠的新常态下,我们将如何面对彼此?
9. 结合笛福(《瘟疫年日记》)、加缪(《鼠疫》)或布莱希特(“Radwechsel”或“换轮胎”)的想法,可以将新冠疫情技治的情况,描述为被流放在家中和对现在缺乏耐心。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种对必然性统治的反抗。在害虫、瘟疫和技术治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力,或者仅仅是以完全无视当前需求为代价。然而,没有必要从禁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监禁”,有可能将明显的禁令视为构成变革空间的限制。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手段,同时,它可能是保持冷静和避免那种由狂热情绪造成悲剧的一种手段。我们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他在1350年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时发现了讲故事的乐趣,并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10. 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不能使世界走向一个减速、可持续和更公平的世界。它宁愿承担如下危险: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上升。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通过一种倾向于现有技术和管理选择的温和技术治理模式来缓解这种紧张——这种技术治理牢记:要想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方式,涉及到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想象。
在一个由客观约束或技术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统治的世界里,一个人看社会、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时,所发生的事情比乍一看要多得多。上述十条建议也一样。尽管意识到了不同的技术模式、替代设计和重组的机会,我们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做的事情上,这给任性的政治和自决领域施加了技术性的压力。如果我们是对的,困境在“新冠危机”刚被宣布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诚然,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德、美三国和其他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也许,紧张关系在中国被一个温和的技术治理所容纳,这种技术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上将技术必要性纳入其中。在德国,紧张关系导致维持一种纯粹的管理政治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温和的不安和不羁的抗议已经导致美国街头的公开斗争。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分析是否有助于揭示潜在的困境,在全球疫情技术圈中强调人际关系的重组,以及将注意力转向技术危机治理的微观政治方面。
注释:
[1] 本文从一个更长的待完成作品中摘录出来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评论。阶段性版本发表于:刘永谋,卡尔·米切姆,阿尔弗瑞德·诺德曼,李保艳译.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J].科学·经济·社会,2021,39(01):10-21.[2] 译者注:克里斯提安·德斯顿(Christian Drosten)教授,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被称为“德国钟南山”。2003年,他是SARS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并且首批研发出SARS病毒诊断方法。
人口与生命系统,或:曲线与直线
作者:安德烈亚斯·福克斯;译:朱颖妤
作者简介: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德国吉森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政治、生命政治和STS研究。朱颖妤,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技术与哲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做的哲学思考——我认为也包含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角度——十分清晰且有说服力。因此,我不会在个别问题上耽搁时间,而是做一个短小的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补充。三位作者准确地谈论了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意义。统计数字、彩色地图、曲线与模拟系统、指标与基本传染数,又一次向社会展示什么是“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福柯)。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人口科学的观点不仅被少数专家和政治决策者急切地吸收,也被受检测的民众热切地去了解。早餐时看一眼发病值和R值已然成为新冠危机时期的晨间祷告。
在当下的疫情控制中,另一种生命政治学的逻辑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大部分时候,它主要存在于哲学评论中,很少被关注到:它就是生命系统(vitale Systeme)的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不同,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主要不是靠人口统计,还要在维持社会技术的功能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关注所谓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容量限制、脆弱性和瓶颈,例如交通、能源,或者是医疗护理。当下疫情的特点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相互影响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随处可见的“拉平曲线”图表中,也许能最明显地观察到这一关系。除了一条明显基于人口科学假设的曲线,还有一条水平的直线显示曲线必须多平坦才能保证医疗卫生系统不过载。生命系统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人口的“凌波舞杆”的角色。灾难阈值会通过人口的感染动态与生命系统的容量之间的交点清晰地展现。就这点而言,不仅要保护民众不受感染,也要保护医疗卫生系统不被过多的病患数量压垮。按假设来说,人口层面的死亡率与医疗系统的容量限制直接彼此影响。人们的生命实际上依赖于像重症监护床和呼吸机这样的技术基础设施要素。这里的一个在交通规划方面同样著名的根本性问题为:如何能保证就算在高峰期也有足够的容量供使用——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火车和高速公路空间?而差别仅仅在于,医疗卫生系统的拥堵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一些人上班迟到了。
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之间有多紧密的关联,还可以从大流行初期检测能力不足的关键性瓶颈处看到。知识基础设施从做检测用的棉签到实验室设备,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的认知基础尤其关键。此外,至少在德国,卫生当局作为关键性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是人口科学和流行病模拟系统的专家们,其作用在第二波疫情中得到突出强调。也就是说,当接触追踪能力过载时,模拟系统通常表明疫情会在人口中更快地蔓延。
简单几个例子已经可以表明,生命系统在疫情控制中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可以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关注问题(matter of concern)。同样很清楚的是,生命系统与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借用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Puig de la Bellacasa)的表述来说,也一直意味着关怀问题(matters of care)。“容量限制”和“瓶颈”(bottlenecks)这些用词有时可能看起来太技术性,但就像一直在强调的那样,医疗卫生系统并不只取决于技术仪器,也取决于护理人员的专门知识(know-how)以及他们如何将那种关怀具体表现出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通常依赖于报酬很低的护理工作。这可能也是这场危机带来的一堂“哲学课”。就像在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中所实践的那样,必须同时考虑技术与关怀(Sorge),而不是像海德格尔一样将技术作为确定的——去-操心的(ent-sorgend, se-curitas)——现代性的命运(Geschick),与此在(Dasein)的原本为之操心的(sorgend)世界的开展(Welterschließung)相对立。
管控与试验间的紧张地带:“精细化技术治理”的轮廓?
作者:史蒂芬·贝申;译:章亚菲
作者简介:史蒂芬·贝申(Stefan Böschen),德国亚琛大学人类技术中心教授,主要从事STS、现代社会理论和风险研究。章亚菲,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2014级硕士研究生。
在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新冠视角》中,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点10中提出了民主理论方面的棘手问题,即严格的技术治理管控与一旁涌动的反叛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他们所称的“温和的技术治理”来调解。
文章中的论述清楚表明,我们的词汇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对立的姿态,并不一定能缓和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事实上,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新冠疫情问题在社会中到底是怎么样被讨论的,以及造成了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独立且不同的观点在互相碰撞,刘永谋等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论点6),也就是“大方案优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该模型以规避风险为原则,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学范式,遵循这些前提来实行相应的专家治国(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这样看来,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危机应对的核心问题是危机时刻过度的技术治理霸权(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我强调一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霸权不存在,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论述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与新冠危机有关的问题。它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的批评,但在文章的论点表述中,它并不能公正地对待激发危机的这些社会认知的复杂性。明确地说:有可能新冠危机首先是社会自我理解的危机,因为我们大肆讨论此次危机的词汇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过时感。这些都有体现在用于描述大流行发生进程的分类和对比中,特别是在批判性地评估大流行遏制措施的成功或失败时。依赖于专业知识去治理国家这一事实成为背景,这种专业知识越来越动态地从根本上建立起来,而危机时期的动态瞬间还呈现出了另一个维度。这个对事实描述尽可能准确的追踪是一个准备好失败的试验,它在这里会成为一个管控问题,也同时展现为一个治理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社会认知复杂性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潜在的巨大威胁和不确定性时,同时有待解决的不同协调合作问题的冲突性场景。和病情相关的现实问题有多严重?怎样最大化地减少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恰当的措施是什么?为了解决危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国家哪些应对危机的途径是合适的?知识不确定性直接转变为社会政治不确定性——反之亦然。同样地,知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也在成为讨论主题。由于室内也存在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情况加剧了管控问题。一部分人对它大肆渲染(“被解放的居家办公中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否定它(“新冠反叛者”),最后一部分人则作为系统相关的人群在身体发肤地经历它(“深受病毒影响的人”)。
在这方面没有简单的出路,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问题,为何不继续放出实验的能量,以便我们不仅能了解知识水平、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之间的复杂纠纷,还能同时将它们转化为实用的策略,从而发掘关于构建这些形势的知识。由于知识的调动极其有限,那篇文章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事实上迄今为止,实验空间被设计得相当具有防御性,从而导致实验空间的局限性,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合法化的逐渐丧失。这种合法性问题能越早解决,强韧的实验结构就能被越早地设计和制度化。只有在自上而下(top-down)的管控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社会实验文化同时展开的情况下,用于克服此类危机的强韧的实验空间结构才能成功实现。不仅在公民社会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这些都要以参与和合作的能力、意愿为前提。这需要相应的民主政策措施设想作为先决条件,以便在大流行面前从制度上确保实验性问题的解决。那样的话,讨论“精细化技术治理”(verfeinerte Technokratie)就变得多余了。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新冠疫情的影响
作者:珍妮·曼德;译:彭家峰
作者简介:珍妮·曼德(Janne Mende),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家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全球治理、国际机构和跨国规范研究。
三位作者为讨论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政治以及技术治理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在下文中,我将讨论这场疫情的技术(甚至是技术治理)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新冠疫情似乎加强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因此,三位作者警醒地提及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2)。他们甚至勾勒出一种日益增长的紧张感,即“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行使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
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这场疫情突显了技术/技术治理和政治层面之间划分的狭隘限制,而且乍看起来似乎还强化了这一的划分。这反而显示了经常使用的“技术统治论”一词的局限性。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效率和——更重要的是——非政治化。
应对公共挑战的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和政治性解决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然而,新冠疫情生动地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技术性解决方案也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与疫情相关的预防、遏制和控制措施,应该是为了保护个人和全体免受病毒的侵害,有时甚至会违背个人意愿。这是大局观(greater good)的逻辑:公共利益可能高于个人利益。
正是这种公共利益和(特定)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似乎引发了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抗议。在这里,我明确地把这种抗议的阴谋论动机放在一边。相反,我考察了那些由觉得其个人利益受到限制,而自己却不认同或不理解(或许甚至不相信)存在更大利益的人所产生的冲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高于其他人的利益,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以至于他们一开始就(以为)没有从公共利益中获益。辨识出其中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作为替代,我将重点放在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上。
在某个时间点上,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取决于某种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再代表非政治化的、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们还必须证明其“输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通常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的形式。然而,即使是最技术化的输出合法性,也与公共利益有关。
[1]效率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有效,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在与需要定义的具体问题相关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对于这两者来说,公共利益构成了一个隐含或明确的参照点。这场疫情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科学家被提升至“权威”的高度(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6),他们的权威必然是通过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来构成其合法性。[2]
因此,政治层面(涉及公共利益的组织和管理)始终是技术和技术治理解决方案所固有的。
然而,谈及公共利益会引出一个问题,即是谁把(哪些)利益定义为公共利益。谁被包括在公共利益的讨论中,谁又被排除在外?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到“投入合法性”(input legitimacy)的民主概念,它是基于公民的参与和代表,以及他们的偏好、利益和个人愿望。
[3]
从投入合法性和输出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这场疫情既不是特殊的,也与常见的治理和政府的组合没什么不同。相反,它放大了所有民主国家和依靠某种合法性和承认(而不是纯粹的武力)的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张力: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投入和输出的合法性之间持续的、可渗透的张力。
[4]
这种张力打开了客观约束(Sachzwang)或技术紧迫性的黑匣子(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引言)。
这种论断并没有为新冠疫情提供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有助于用更加熟悉的术语来描述随之而来的挑战。至少在这一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我们可以建立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之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辟新的道路,实际恰恰相反。在此背景下,我提出了处理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三个要点。
首先,必须克服技术性/技术治理和政治性解决方案之间的截然划分——但不是简单地被消解。相反,它们彼此依赖:技术专长以政治和社会合法性为基础,就像政治解决方案依赖于技术专长一样。如果不将技术和技术治理的解决方案假定为非政治性的,那么它们的政治影响和效果可以被更清楚地加以处理和讨论。
第二,描述这场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需要重塑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理性信念,与对这些措施的非理性反对之间的明显对立。这样做可以促使双方进行对话,以防止他们进一步疏离。(当然,这并不是指激进的和极端主义运动。)它还可以有效防止“反叛的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援引人权和自由来支配政治领域”的假设(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相反,强调技术性、技术治理和理性的解决方案的政治层面有助于重新获得这些参照点。人权作为一个参照点,特别是为强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创造了一个基础。在那些利用公共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以至于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人权也有助于率先产生这种联系。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确保实现人权。
[5]
第三,任何可行的疫情防控方案都不能简单地无视个人利益而支持公共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相反,必须维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投入和输出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以平衡和调和这两者,以至于不会忽视掉任何一方。在疫情期间保护公共利益可能确实需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它保护了某些个人利益(如健康),也抵制了其他利益(如不戴口罩或或朋友见面)。
同时,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必须是一个包含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声音的广泛讨论的问题。有各种(有时虽然是困难的)措施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制定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和决策方面的高度透明(这也有助于沟通与新挑战有关的试验和错误)。这些措施亟需包括强有力的地方性对话、包容和合作议程,以加强个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包括对社会其他团体和公共利益)。措施还包括国际和全球合作,
[6]
以及为个人在地方层面上被要求表现出的那种团结和责任感的产生树立起榜样。最后,措施必须包括考虑公共利益的多元化。除了公众健康,还包括人权、体面的生活条件和性别平等,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总之,这些措施有助于强化技术性、技术治理和专家的合法性与公共利益,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个人利益不会简单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尤其是在涉及到(其他)每个人享有人权的时候。虽然它们也很重要的。如何权衡这些利益的问题不仅对当前疫情而言是一个挑战,也是对所有基于某种合法性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constellations)的挑战。
注释:
[1] Jens Steffek: “The output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public interest,” International Theory7/2 (2015), pp. 263–293. Fritz W. Scharpf: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 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Working Paper3/1 (2003).[2] Janne Mende: “Business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Beyond public and private,” 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P IV 2020–103 (2020). https://www.econstor.eu/handle/10419/218731. A. Claire Cutler, Virginia Haufler, and Tony Porter, eds., 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lbany: State New York UP 1999.[3] Scharpf: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4] See Tanja Brühl and Volker Rittberger: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governance. Acto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ittberger and Volker, e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okyo, NewYork: United Nations UP 2001, pp. 1–47. Vivien A. Schmidt: “Democracy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visited. Input, output and throughput,” KF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Europe Working Paper 21 (2010).[5] Janne Mende: “Are human rights western –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7/1 (2021), pp. 38–57.[6] Armin von Bogdandy and Pedro Villarreal: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vaccinating against COVID-19. Appraising the COVAX Initiativ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Paper 46 (2020). Michael Ioannidis: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solidarity. COVID-19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order,”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4(2020).
作者介绍:
刘永谋(Yongmou Liu),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哈佛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访问学者、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法国索邦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迄今出版《技术的反叛》《物联网与泛在社会的来临》《哲人疯语》《行动中的密涅瓦》《思想的攻防》《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导论》《警醒中国人》等著作20余种,发表中英俄德文学术论文140余篇,多次受邀在荷兰、西班牙和美国举办学术报告,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注意。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
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被国际技术哲学界尊称为“Old Brother”,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首任主席,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专业的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的国际讲席教授。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米切姆都试图厘清现代科学、工程与技术在其创造的世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出版的作品包括《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中文版于2008年出版)、《伦理与科学:导论》(与亚当·布里格尔合著英文版于2012年出版)、《迈向工程哲学:历史哲学视角和批判性视角论文》(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委员会(1994-2000年)和欧盟委员会专家研究小组(2009和2012年)的成员。所获奖项包括国际世界技术网络(WTN)伦理奖(2006年)和西班牙瓦伦西亚国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
具有国际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以技性科学理论著称,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科学史与哲学专业以及技性科学史与哲学专业教授。自2013年以来,他编辑出版了《技性科学史与哲学》系列丛书。他利用技术哲学来重建研究实践,不仅是为了达成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更是为了了解参与事物运作的方式,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技术理解。与此相关,他对构成原理以及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的专著包括《维特根斯坦导论》和《技术哲学导论》。他还是《技术与语言》(Technology and Language)期刊的首席科学编辑。
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
是德国吉森大学社会学系“碳泡沫和搁浅资产”研究项目(由德意志科学基金会DFG资助)的首席研究员。2017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灾害治理与重要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目前凭借在生命政治、安全、环境政治、能源和金融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领域开展(批判)社会理论的讨论来开展研究。最近的出版物包括:《复原的安全装置:灾害风险与生命政治的重要系统》(2018)、《冻结时间,为未来准备:作为当前安全问题的储备》(2019)。
斯蒂芬·贝申(Stefan Böschen),
亚琛大学人类技术中心(HumTec)社会与技术专业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担任KIT技术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ITAS)的“知识社会和知识政治”领域的资深研究科学家和研究组组长。具备化学工程培训(证书)、博士学位以及特许教师资格。特别研究兴趣在于科学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现代社会理论。运作的项目包括:“复杂伦理学”(BMBF,2017-2020)、“弹性电网(FEN)研究园区:社会-经济直流电”(BMBF,2020-2025)、“新冠病毒区隔”(大众汽车基金会,2021-2022)。已发表《身份政治:参与性研究及其与社会和知识控制相关的挑战》(Böschen, S.; Legris, M.; Pfersdorf, S,2020)、《混合知识体系:社会学场域理论概要》(Böschen S., 2016)、《实验性社会:作为知识经济装置的实验》(Böschen S.; Groß, M.; Krohn, W.[Hrsg.], 2017)。
珍妮·曼德(Janne Mende),
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家法研究所研究小组组长。她曾担任达姆斯塔特理工大学跨国治理专业副教授、吉森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班贝格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员、卡塞尔大学发展与体面工作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人权、全球治理、国际机构和跨国规范。她的出版物包括《全球治理与人权:公私合作》(2020)《文化与身份的人权?集体权利的矛盾》(2016)、《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正当化模式:调和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2011年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