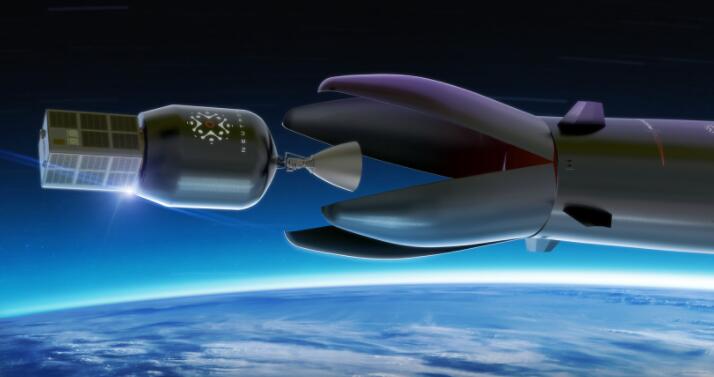来源:界面新闻
记者 |司林威
2020年7月15日,晓明在云南省澜沧县的深山里辗转了十四个小时,终于从边境偷渡到了缅甸。当时,年仅21岁的他告诉家人要出去上班,背上一包行李就跟着蛇头的脚步来到了异国他乡。
99年出生的晓明是家中独子,中考失利后,他去上了一所中专职校。在从事了修理工等各项工作后,因为疫情失业在家的他正苦恼着。此时,一位初中的“好哥们”联系上了他。
这位老同学正在缅甸从事“网络诈骗”。明知是违法犯罪,但缺钱的晓明经不住诱惑,告诉家人说要出去上班,便只身前往缅甸。
这一切也成了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境外“诈骗团伙”
趁着深夜进入中缅交界的深山,一直赶山路到第二天中午,晓明终于偷渡至缅甸境内。诈骗团伙早已安排好汽车来接,晓明交上身份证做抵押,付出100元人民币的路费,随车被送至缅甸佤邦旗下贺岛经济开发区。
佤邦地处缅甸北部,与我国云南省接壤。贺岛经济开发区是个典型的混乱地区,“赌场、红灯区、吸毒随处可见。”晓明说,这里也聚集了大量从国内来的从事网络诈骗和网上赌博的人群。
随着中国警方对“网络诈骗”的严厉打击,一些长三角、珠三角的“诈骗村”早已消失,化整为零的他们纷纷逃向了国外,东南亚成了新的聚集地。
晓明老同学所在的团伙有两个根据地,一个在缅甸佤邦北部的勐波县,负责“前台”工作;一个在缅甸佤邦旗下贺岛经济开发区,负责“后台”工作。
“怕被一锅端,所以特意分开。” 晓明解释说。诈骗团伙的“前台”和销售工作类似,负责源源不断地寻找受害者并将她们的财产“榨干”。而“后台”则管理投资网站或者博彩网站的数据,并充当客服,负责做骗后的收尾工作。
B站反诈UP主“TOM表哥”曾潜入过众多诈骗分子的后台,发现它们都为诈骗量身定制了完善的功能。比如博彩游戏网站,可以随意控制游戏倍率、输赢,查看用户隐私信息,还能一键消除记录。
“TOM表哥”透露,这些技术产品背后都有着完善的黑色产业链相助,往往诈骗团伙自己并不需要懂计算机技术,有专门的外包公司负责售卖这些系统。“这些公司明知客户是诈骗分子,但只会装模作样地在售卖时写上一句本产品只提供技术支持,其余一概不负责。”TOM表哥称。
晓明的同学正是诈骗团伙的后台主管。他顺手将不善言辞的晓明也安排在后台工作,并给晓明开了一份不错的薪水。第一个月工资八千元,第二个月涨到九千,第三个月涨到一万后不再上涨,直接现金或者银行卡付款。
而前台们人数众多,但往往没有固定工资,完全依靠诈骗所得的赃款进行提成。据晓明透露,提成比例大约是20%左右,这意味着前台们骗来1万元,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收入。
据晓明介绍,在缅北像他们这样从事诈骗相关产业的“公司”众多,他所在的团伙有近五十人,规模算小的,有一些团伙甚至达到数百人。
寻找“猎物”
在转账10万块之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星薇从未想过,日日嘘寒问暖的“老乡”会是一个骗子。
2019年3月份,星薇在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3000块的月薪虽不算多,但在她生活的城市,这笔钱也足够满足一个年轻人的日常所需。星薇每个月还会用剩下的钱,为衣橱里添些新衣服。
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入职一段时间后,星薇发现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不约而同玩起了交友软件,出于好奇,她也下载了一款线上交友的APP,上传自拍照当头像,填写居住地,很快就完成了注册。
几天后,就有一个“老乡”来跟她打招呼,并且加上了微信。“老乡”自称赵老师,说自己是专业的护肤老师,平时很忙,要跑全国各地的学校给大家讲课。
但“忙碌”的赵老师总是能抽出时间对星薇早安晚安嘘寒问暖,还会分享自己生活中发生的趣事。“没想到还挺投缘的,我说什么他都接得住。”星薇这样评价刚开始的互动。
这样火热的聊天持续了几个星期后,赵老师把她拉近了一个护肤知识讲解群,群里大概有四百多人。在赵老师一系列的话术套路和群友的配合下,星薇同意了购买几百块的护肤品小样。
之后,星薇还陆陆续续购买过一些产品,直到赵老师向她推荐一套10万块的“专属护肤品方案”。星薇说,她最初是想拒绝的,但是架不住赵老师的情绪绑架和怂恿,收入不高的她一口气办了8张信用卡。“我之前没用过信用卡,这钱花起来也没什么概念,不知不觉那10万块就被分开刷掉了。”
晓明说,这就是典型的“杀猪盘”套路。像星薇这样的年轻女性,正是网络诈骗团伙最爱的目标。
“TOM表哥”曾潜入过一家类似的化妆品销售公司,他搜集到的内部资料里写道:我们的核心群体是三四线城市有爱美之心的女性,厂妹、护士和离婚人士都是我们的优质客户。
诈骗团伙一般会在各大社交媒体和交友软件上寻觅“合适”的对象。首先,他们利用社交账号打造各类精英“人设”,然后以交友的名义接近女性,无论未婚已婚,只要有机会,他们绝不放过。
在其他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中,诈骗分子经常冒充自己是电商平台、或者“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第一时间降低你的疑心,他会主动透露一些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甚至包括你的家庭住址,购物清单等。
在黑灰产业链中,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倒卖潜在受害者的个人隐私信息。这些人在业内被称作 “菜商”。
蚂蚁集团反诈安全专家勉哲解释道,“菜商”主要通过木马寻找漏洞,或买通平台内部人员,或者暗网买卖等方式搜集各类隐私信息。然后把各种信息拼接关联到一起,形成一份完整的数据。诈骗团伙在将“剧本”培训熟练后,就会找“菜商”买来自己想要的“猎物”信息。
精心设计的套路
盯上“猎物”之后,诈骗团伙的每一步都是精心准备,环环相扣的。
晓明说,以经典的“杀猪盘”套路为例,如果对方是年龄大的女性,诈骗分子就会说自己是感情受挫、离过婚的金融圈人士;而对于一些年纪小的女性,就打造一个导师形象,扮作一名优秀的高富帅。“朋友圈的照片,发布的社交内容,聊天的台词,每一句都会按照“剧本”来走。”
随着技术的发展,不管是语音电话还是视频聊天,犯罪分子都可以利用工具进行伪装,加强自己“人设”的说服力,降低对方的防备心。而一些涉及心理学的“话术”和“控制”技巧,也早已被总结提炼出来,供诈骗分子套用。
等到关系熟了之后,利用自己的精英形象,诈骗分子就开始将受害者引流至炒股或者博彩网站,说自己能精准预测,带她们挣钱。
作为后台人员,晓明可以随意控制这些网站的结果,涨还是跌,大还是小,单还是双,全在掌控之中。“想让她赢就赢,想让她输就输。”而已经沉迷在“导师”、“男友”甜言蜜语中的受害者还以为恋人可以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一开始,诈骗分子只会让受害者充值几十元试试,带她“赢”几把,让她感受到“导师”或“恋人”的专业性,之后再一步步加码。随着受害者对于赚钱的贪念加深,“导师”就会怂恿她们充数千至上万元。
一旦大额金钱转入,受害者就会发现自己的账户无法提现,而这时“导师们”就会准备“脱身”,引导她们去找赌博平台。这时,扮演客服的晓明就会负责稳住她们,并告诉她们想要提现,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流水,即充值更多钱。
前台的“导师们”这时候还会出来安抚受害者的情绪,告诉她们钱没了可以再挣,自己也会去赚钱,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很多受害者往往到最后都没有意识到罪魁祸首就是她在网上的“导师”、“男友”,而是去咒骂博彩平台,或向平台哭诉自己的遭遇,乞求还款。但控制这一切的犯罪团伙,已经开始收割下一个目标。
从事这样的“工作”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晓明心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公司的洗脑文化又一遍遍冲刷着他。在这里,“赚钱”主导一切,墙上的标语贴满了各种励志口号,“用业绩证明自己”,“一切为了家人与自己”。但内心深处,晓明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是一块“遮羞布”,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能睡着的借口。
据晓明介绍,团伙里也有很多人对这些口号深信不疑。“他们愿意接受这个谎言,把‘奋斗’的谎言当做现实,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晓明苦笑说。
洗钱产业链
诈骗团伙收到转账后,最关键的就是“洗钱”。这一环节集中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也是反诈工作中较难的部分。据“TOM表哥”透露,诈骗分子所得赃款中,可能近三分之一都需要损耗在“洗钱”过程中。
“TOM表哥”解释到,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拿自己的银行卡让受害者转账,这样很容易就被警方追踪,他们往往会到“跑分平台”下单寻求“洗钱服务”。而所谓“跑分”,分指的就是钱,跑就是让钱流动起来,使它难以追踪。
专门的“跑分平台”会招聘很多兼职的“卡农”——即提供大量银行卡的人。这些“卡农”在跑分平台缴纳押金后,就可以接取洗钱单,卡农们层层分级,一个总代理接到一个大单,会分成数个小单让底下的“卡农”去执行。这些卡农用手中的大量银行卡层层转账,使得银赃款去向难以追踪。
而诈骗分子为了吃到这笔即将到嘴的肥肉,还得再经过一道“地下钱庄”的洗钱。这部分的黑产,现在已进入“虚拟货币”时代。
得益于“泰达币”等虚拟货币无国界、无需实名的特点,地下钱庄往往会将赃款汇入一些交易平台,将其转化为虚拟货币,再将资金转移至国外账户变现。或者使用“虚拟货币”混币服务,再走币圈的“OTC”(指法币出入金)渠道变现成法币,诈骗分子最终得以将赃款洗白。
而这样极其专业复杂的洗钱手段,给警方反诈工作提供了新挑战。2021年5月,沈阳警方在市区内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将一伙正在跑分的犯罪团伙抓获。该团伙仅有3人,利用通讯软件与境外诈骗窝点勾连,在沈阳大肆收购银行卡,为诈骗团伙提供“跑分”洗钱服务,涉及资金流水近9000万元人民币,3人从中非法获利180余万元。
而这只是黑灰产业的冰山一角。蚂蚁集团反诈安全专家勉哲总结强调黑灰产业链呈现出越来越碎片化的趋势,分工越来越细化,不同业务之间并不相互联系,“你抓到了一个人后,他背后的对接的那个人也很难抓到。”
“TOM表哥”也注意到了这些细节,他发现诈骗分子为了防止留下过多证据,往往会每一个环节变一个平台。例如先在短视频平台引流,导入到社交软件上,又引导受害者使用会议类软件沟通,转账时会用各种借口要求受害者转入不同银行卡中。
没有硝烟的对抗
2021年9月,苹果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第一的应用悄然变成了一个新面孔——“国家反诈中心”,其短期下载量直接超过了微信、抖音等国民级应用。此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还同时登顶了多个安卓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这款应用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开发,发布于 2021 年3月,旨在为用户建立电信网络诈骗涉案举报通道,并增强防范宣传。为了向更多人宣传这个应用,河北秦皇岛的民警老陈还登上了热搜,他在快手直播中使用“连麦PK”功能,与网红主播进行互动,号召大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还有更多人在背后默默付出,守护着人民财产的安全。
在2020年,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曾发起“净网2020”打击网络黑产犯罪集群战役,重拳打击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水军等突出违法犯罪提供网号恶意注册、技术支撑、支付结算、推广引流等服务的违法犯罪活动。共侦办刑事案件4453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311名(含电信运营商内部工作人员152名),查处关停网络接码平台38个,捣毁“猫池”窝点60个,查获、关停涉案网络账号2.2亿余个。
今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在京联合启动“全社会反诈总动员”全国反诈防诈系列宣传活动,为新一轮反诈工作拉响了号角。
虽然现在大部分网络诈骗分子都躲在境外,但是,处在反诈斗争一线的各地公安干警们也在紧跟形势,克服种种困难将犯罪分子捉拿归案。比如今年上半年,湖北警方就发现一家名为“永隆公司”的诈骗团伙通过熟人邀约的方式,鼓吹到缅北工作包吃包住赚大钱,而这个地点正是晓明曾去过的勐波县。
一批批本地青年在“赚钱”的诱惑下,辗转偷渡至到缅北,然后从受害人沦为诈骗集团的帮凶。和晓明经历的一样,该公司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从诈骗准备、筛选对象、键盘手包装、交流话术、实施诈骗、洗钱通道及诈骗平台技术保障等均有专人负责,集团成员多达100余人,所从事的骗局正是专门狩猎女性的“杀猪盘”。
据警方披露,“永隆公司”涉案100余起,涉及受害人400余人,均为女性,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最高受骗金额60万元。最终11月2日,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对外宣布破获“6·11”电诈专案,经过警方十个月的努力,抓获犯罪嫌疑人93人,涉案金额3000万。
沉重的代价
星薇在花了10万块之后,还在和赵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赵老师并不关心她是否还得起信用卡欠款,只是隔三差五找机会要她继续购买产品。等星薇终于确信自己被骗后,赵老师的微信账号已经被封了,“老乡”消失在她的朋友圈。
2020年6月末,催款的电话和短信越来越多,银行催款的人甚至去了星薇的老家。星薇的爸妈知道后,拿出8万多帮忙还了一部分债务。“这笔钱本来是他们用来买车的。”星薇自己的生活也很紧迫,每个月工资的一大半都打给了银行,只能留下几百块用于日常开销。
为了省钱,她不再买新衣服,每天都会自带午饭去上班。
“你知道抑郁症和焦虑症吗?”星薇说她会无意识抠手指,很使劲那种,上网一查才发现这是心理问题的一种表现。
而在贺岛待着的一个多月里,晓明一边从事着诈骗工作,一遍继续骗着家人说在外面上班,但内心的挣扎愈演愈烈。
晓明说,他冒充客服面对受害者时,有时也会动恻隐之心,他会故意将话术留出一个明显的漏洞,希望对方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不要再充钱进来。
但这些深陷骗局的人此时已难以分辨真假,往往都不会理会晓明的暗示。看着她们一个个羊送虎口,晓明于心不忍,“但我又不能说的太直白,一旦被发现,我在缅甸也就回不来了。”
让晓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的遭遇。一位刚刚生产完的年轻妈妈,由于和婆婆及丈夫关系不好,独自带着小宝宝生活。这让诈骗分子找到了可趁之机,在诈骗分子的嘘寒问暖下,年轻妈妈逐渐沉浸在网上世界的感情中。
为了榨取她的价值,网上的“恋人”怂恿她离婚分家产,并承诺给她未来。等到这个年轻妈妈以为离婚后可以拥有真爱时,又继续怂恿她将离婚分得的财产变现。于是她将汽车卖掉,得来的钱都投进了博彩网站,想要为爱的人博一个美好的未来。直到这笔钱“输光”,“恋人”又让她去借贷,利用各种借贷平台继续充值,等到她的经济价值耗尽,“恋人”就消失了。
此后,她的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每天都来找平台要钱,哭诉自己的遭遇,看着她发来的照片,晓明说有些受不了,“憔悴得根本不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这件事埋在了晓明的心底,“非常难受,但又找不到东西发泄。感觉自己无能为力,一个人又无法改变什么。”
又做了一个多月,晓明回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等到“公司”转型准备开发新骗局时,晓明找到了脱身的机会。由于后台负责人是他同学,诈骗团伙并没有为难他,并为他承包了来回偷渡的费用。
再次在边境的深山辗转了9个小时,晓明终于回到了国内。他向家人坦白了自己所谓的工作,就是从事诈骗,家人们十分震惊,并劝他去自首。
最终,晓明选择了主动坦白。由于认罪态度良好,且协助警方侦查案件,他被“取保候审”。年仅22岁的他,现在还在等候着案件的开庭,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不管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再去做了。”晓明说。
(记者林北辰亦对本文有贡献,文中晓明、星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