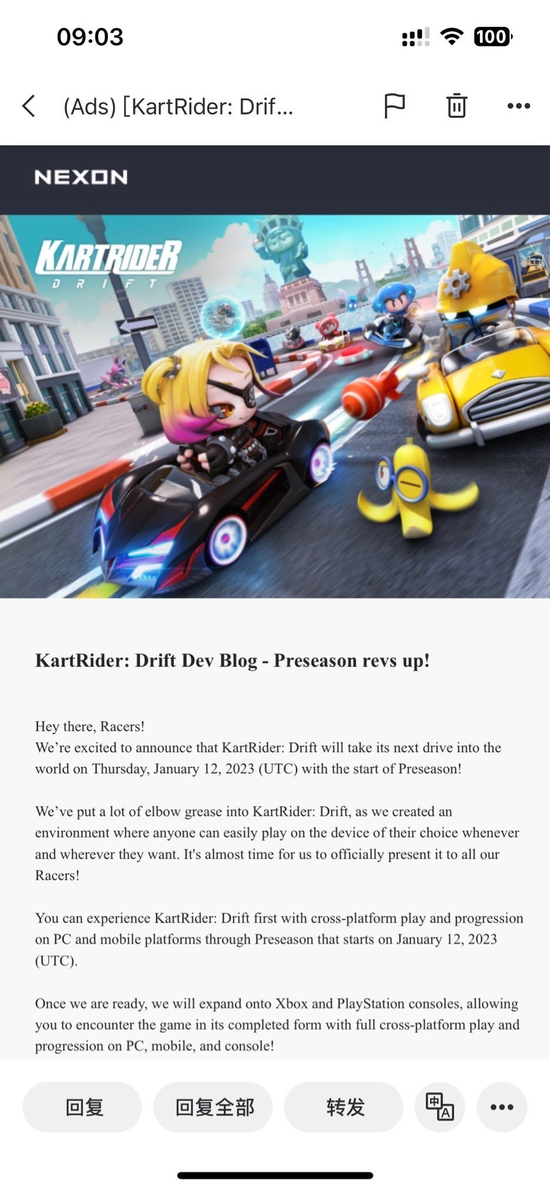今天,分享一篇与邮递员往来的日子,希望以下与邮递员往来的日子的内容对您有用。
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穿“正式制服”的人就是邮递员。一身深绿色工作服,戴一顶深绿色大檐帽,脚穿绿色胶鞋,骑着深绿色自行车。自行车上挂着两个绿色的挎包,横跨在后车座两侧。挎包里面总是装满报纸、书刊、票据、汇款单之类的东西。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松嫩平原上的一个偏僻乡村度过的。负责我们村的邮递员叫杜光辉,平时大家都叫他小杜。自行车铃声一响,准是他来了。那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当兵,母亲听到铃声就早早地等候在大门口,盼望能有哥哥的来信。
有一次,小杜去大队部送信,正赶上村干部外出,开会的开会,下屯的下屯,只留下“铁将军”把门。小杜到我家的时候,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地址是重庆,便知道是二哥寄来的。
我拿到信后刚要进屋,小杜扭扭捏捏地对我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大队部锁着门嘞,报纸送不进去,你能帮我转交给他们吗?”我很乐意地答应了。小杜便把一大摞厚厚的报纸和杂志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抱回家后,打开报纸,看到了《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还有《红旗》杂志,我像久旱的大地遇到甘霖一样,贪婪地读起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比物质生活更贫瘠。在报纸版面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副刊,相声小帽、二人转、单出头、拉场戏、小快板、小戏曲,什么都有,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文学创作的。
从那以后,小杜知道了我的心思,每次除非有挂号信或者汇款单,他干脆不去大队部了,直接把报刊交给我,我看完后再给大队部送过去。那一时期,我在报纸副刊上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阅读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和小杜成了忘年交。有好几次他送信到我家,正赶上大雨倾盆,便在我家避雨。赶上家里吃午饭,我和父母亲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但他坚决不同意,说邮电局有规定,不许在服务对象家中吃饭和收受礼物。
1982年,我从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汽车队当修理工,过上了吃食堂住宿舍的生活。此时,小杜也被调回县里,负责我们单位所在区域的报刊投递工作,我们又打上了交道。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文学迎来了繁荣的春天,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买书、订杂志成了我基本生活费以外最大的花销。我订阅了《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杂志,每次杂志要送达的日子里,我都焦急地等待着小杜。特别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小杜更是帮了不少忙。那时投稿都是邮寄信件,短稿信封就能装下,长稿需要档案袋那样大的信封,稿子装进去粘贴封口,不用贴邮票,在信封的一角剪一个小口,写上“稿件”二字,就邮寄出去了。到年底,各报刊与邮电局都是“邮资总付”的。每一份投出的稿件,我都要记录并计算投稿时间,如果三个月没有收到用稿通知,就转投别的报刊。
小杜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绿色天使,更是我的知音。一个周六的中午,单位发了补助费。领导给我们放了一下午假。家在县城的都回家了,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待在收发室。外面下着大雨,我想今天小杜要晚来送报刊了。随后,清脆的铃声就响起来了。我赶忙把小杜拉进了屋里,他把雨衣用来包裹那个大大的邮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我说你这样是要感冒的。他笑着说邮包里都是报刊,还有给我的汇款单。他解开雨衣,拿出来我单位的报纸,我代替收发员盖了收发章,走了签收流程。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随即又递给我一个大纸袋,还有一张105元的汇款单,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款项,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60多元。我撕开了那个大纸袋,是一家省级文学杂志,翻到目录页,看到小说标题和我的名字后,小杜和我都开心地笑了。
后来,邮电局改成了邮政局,又分出了电信局。邮政局的业务逐渐淡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视线。很少有人写信汇款了,也几乎没有人订杂志了。似乎邮递员也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职业。小杜早已变成老杜,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子杜雨露也在邮政局工作,也是投递员。
我虽然一直从事写作,但情况已不同。写稿已不再用笔,电脑打字代替了手写。投稿通过电子邮箱,发稿费不再用汇款单,而是用银行卡。有时编辑直接把稿费打到作者微信里。但我还是与老杜和小杜保持着联系。没事的时候我就约杜光辉出来吃饭。他现在70多岁,我也快退休了。我俩一瓶白酒,席间,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啥都聊。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报纸和杂志。
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杜光辉的记忆力超级好,多年前的事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能背下来每一本杂志的创办地,是月刊、双月刊还是季刊,甚至杂志的邮发代号都能记住。他说当年邮递员送信送报纸都是骑自行车,现在城里送信是用有车篷的电瓶车,到乡村是开客货车去,真正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
时代发展得太快,但我坚信邮政局的使命一直还在,邮递员的光辉也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要端起青春的酒,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共同干杯。
(作者系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