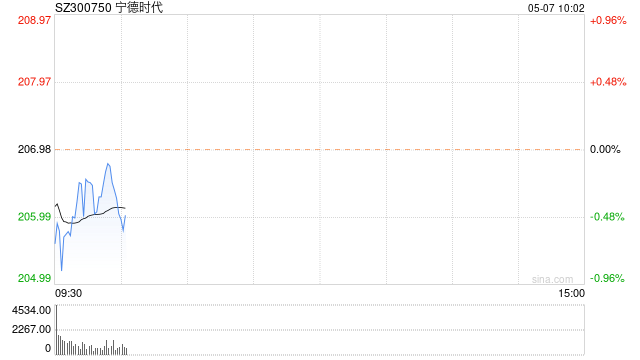今天,分享一篇当科学家也成为“风口”上的弄潮儿,希望以下当科学家也成为“风口”上的弄潮儿的内容对您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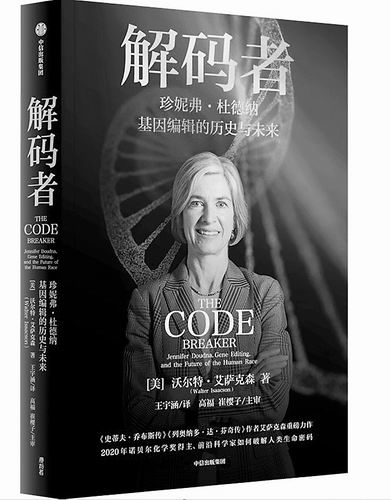
《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王宇涵译,高福、崔樱子主审,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出版,定价:79元
■吴晨
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可能带来产业的大爆发,也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尤其是与我们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基因科学。试管婴儿的诞生给不孕的夫妇带来了福音,同时引发了不小的伦理讨论。20世纪90年代克隆羊多莉诞生,赢得科学界的一片喝彩,却也带来人们对克隆人的担忧。2018年首例基因编辑胎儿的诞生,遭到全球科学家的围剿。
人工授精、基因排序、基因筛查、基因编辑、胚胎实验,看似递进的步骤,却越来越逼近生命本源的核心问题。这既是基因科学的魅力所在,又让人战战兢兢,因为人类可能将掌握改造自身的钥匙。
一方面它神秘莫测,技术的进步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赋予科学家近乎“造物主”的角色,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它又充满巨大的商业机会,尤其像CRISPR基因编辑这样的新技术,可能在治疗遗传疾病、根治癌症、延缓衰老、定制化医疗等诸多领域大显身手,将会撬动7万亿美元的全球医疗大市场。
名与利的交织、科学与伦理纠缠,让探索基因科学这一人类科技的前沿变得错综复杂。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杜兰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艾萨克森在《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以下简称《解码者》)一书中很好地剖析了这种复杂性:当硅谷找寻下一只“独角兽”的孜孜以求遭遇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协作与创新,当名利驱动对科学圣杯的激烈竞争遭遇好奇心带来的偶然的科学发现,探索科学前沿便不再单纯。商业利益的驱动、名利双收的渴望,是拓展新疆界的动力,但对科学探索而言,不应是全部。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宣布授予两位女科学家——美国人杜德纳和法国人沙尔庞捷时,全球轰动。
首先这是对女性在科学领域内所取得突破的认可。其次,诺贝尔奖在认可新科技方面明显提速,杜德纳和沙尔庞捷因为发现CRISPR而获奖,而CRISPR刚刚引发全球对基因科学发展的关注热潮。当然,杜德纳研究的RNA(核糖核酸)在2020年也大放异彩,基于mRNA(信使RNA)迅速开发出的新冠肺炎疫苗成效显著。最后,另一位在CRISPR领域内成果颇丰的华裔科学家张锋这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也引发了诸多猜想。
可以说,贯穿《解码者》的一条主线,正是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两大创造者杜德纳和张锋之间的竞争。杜德纳发现了CRISPR可以应用于基因编辑,并在试管中完成了实验,但是没有在真核细胞或人类细胞中开展实验。当她的论文发表之后,各路科学家都意识到谁第一个完成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实验,谁就有机会能获得名望,并会成为基因编辑商业化的受益者。
张锋则是第一个在人类细胞上尝试这项技术的科学家,其贡献足以获得诺贝尔奖。他与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同一时间入学哈佛。科学界认为,几十年后两个人当中到底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多变化,尚未可知。可见,张锋的科研实力和基因科学的应用潜力得到了多方认可。
用CRISPR编辑基因,可能会带来更简单、更准确的各种疾病筛查机制,用CRISPR的基因编辑功能可以对各种致病基因发起直接的攻击。一系列潜在的医学应用让CRISPR成为未来各路资金争夺的对象。
杜德纳团队与张锋团队之争凸显了过去20年商业、投资、创业对科研的渗透所带来的变化,而这20年恰恰是基因科学加速发展的时代。
1952年,当索尔克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时,他根本没有想过申请专利,因为这是造福人类的发明;20世纪70年代,当转基因技术发明后,科学家也并没有忙于创立公司,而是召开了第一次基因界的大会,讨论是否需要对改变生物基因构造的科研,即人可能扮演“上帝”的角色,设定边界和规则。
但CRISPR被发现之后,却引发了一系列专利权的争夺。硅谷文化对美国东西两岸学界的影响已经很深远,一旦有好的发现,科学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公司、引入投资人、招募专业管理团队、研究赚钱的应用场景,甚至在他们撰写的论文最后,也都会对潜在的商业应用场景进行富有前瞻性的描述。
新的成功算式变成了“基础科学研究+专利律师+风险投资=独角兽”,科学家也成了“风口”上的弄潮儿。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科学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重心被放在了惊人的研究、明星效应、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抢先成为“全球第一人”之上。
这也意味着科学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合作越来越难。杜德纳团队与张锋团队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背后两所院校之间在CRISPR领域争取第一的竞争和随后的专利之争,最具代表性。
过去一百年,人类在物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无疑,基因科学也是其中之一。
但基因科学的发展也引发了各种讨论,涉及伦理、人性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基因克隆技术制造的多莉羊诞生,就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心。适用于动物的技术同样可以用在人身上,但人能够扮演“造物主”的角色吗?CRISPR的发现也引发了类似的讨论。如果我们为了胎儿的健康,用CRISPR修改胚胎的基因,会带来什么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了治病而编辑筛除致病的基因,大多数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给胎儿添加新的基因,一旦允许这么做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比如我们已经找到有利于运动发展的基因,未来也可能发现让人的大脑变得更聪明的基因,如果人类把这样的基因植入子代的胚胎,就可能制造出“超人”。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规则会不会因为基因编辑而被打破?如果基因编辑很贵,只有有钱人支付得起,而他们通过基因编辑让下一代更聪明、更健康,是否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甚至再现只有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才会出现的全新种姓社会?
此外,一种基因并不一定只带来一种结果,致病基因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其他好处。例如导致镰状细胞贫血的是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如果父母只有一人有这一基因,孩子身上的突变基因就以隐性状态存在,不仅不会导致贫血,还可以预防疟疾。换句话说,突变基因是非洲黑人进化出来抵御疟疾的基因。如果为了根治贫血而筛除这一基因,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人类对自身基因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简单地添加和删除基因,忽略它们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如同玩火。
杜德纳主导了2015年的基因编辑伦理和规范的研讨会,当时焦点放在是否应该允许基因编辑用于人类实验,尤其聚焦在是否应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产生可遗传给下一代的新基因。
这是非常敏感的领域,两派意见也非常鲜明。保守派觉得科学家不应该扮演改变人类的“造物主”的角色;激进派则认为,如果有机会改善人类的基因,为什么不去尝试。讨论折中的结果是,在无法确保基因编辑对人体无害之前,不应该从事可遗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编辑工作。
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法约束个别科学家的冒险行为,尤其在成为“世界第一”很可能带来巨大的名利的情况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让科学探索回归本来的轨迹。治疗新冠肺炎的紧迫性让基因科学家之间开展合作,以及与其他跨领域的研究者协作,变得十分重要,也让科学合作回归开源、协作、共享的道路。
利用CRISPR快速检测新冠病毒,利用基因编辑工具帮助人类对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产生免疫力,是基因编辑工具最基本的应用场景。过去两年,无论是杜德纳还是张锋,都忙于实验与开拓,并在这一领域有不少创举。
新冠肺炎让科学家重新意识到,他们职业的崇高之处不在于谁是某项科学发现的第一人,或是谁靠发明赚取了第一桶金,而是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是应用科研解决实际问题、造福全人类的能力。
科学发现的基础是好奇心,是相互协作,绝对不是金钱和名利的诱惑。科学也需要贯彻长期主义,是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成果。我们在记住那些“偶然”获得阶段性突破的名人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同样做了大量工作和贡献的同时代人。
关于这一点,杜德纳和张锋很清楚。确切地说,CRISPR不是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发现的。CRISPR的发现源于许多科学家的好奇心和运气。
鉴于许多基础科学的突破得益于政府基金,而大学和研究者却因为突破应用的商业化而获益,有科学家提出,应该把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收益重新投入政府基金中,一方面补充政府对基础科学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帮助科学家回归正常的合作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类似CRISPR这样的突破性发现能够被广泛推广,成为基因科学和相关医学应用的主要推手,还是得益于产学研背后的商业驱动。但如果商业利益过大,科学家之间的协作被专利权之间的交易取代,就可能催生不良的科学文化:为了追求第一,追求名利,而不顾一切。
此外,不能把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混同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成功制造mRNA疫苗的生化公司莫德纳的董事长努巴尔·阿费扬就指出,生物化学和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与高科技企业平台化和寡头化不同,生物化学领域的游戏规则不是赢家通吃,甚至不是简单地比拼速度,科研之间的依赖性更强,更需要分享成果,协作共赢。
这恰恰是重新认识科学精神的关键:科学精神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的不断求索,而新冠肺炎带给人类的最大启示是敢于跨越。
(本文系《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一书序,标题为编者所改,内容有删减。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