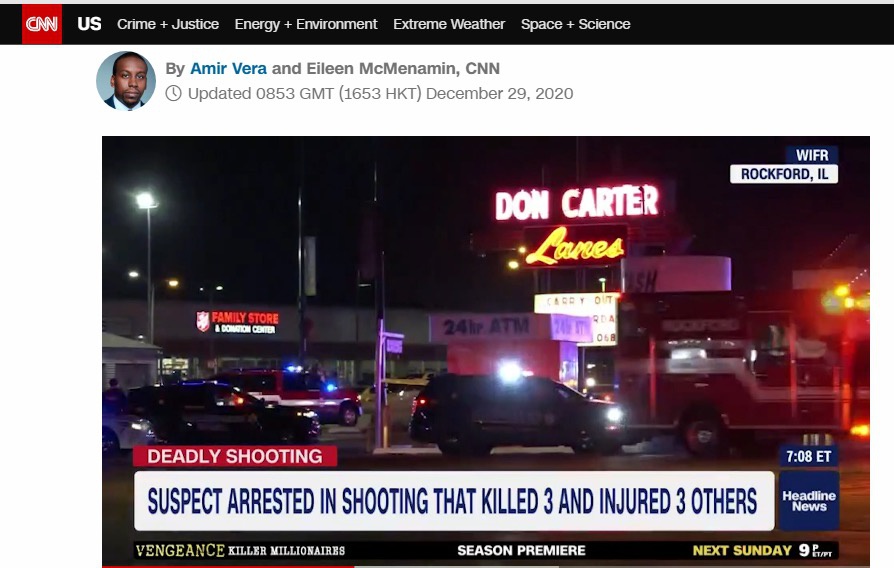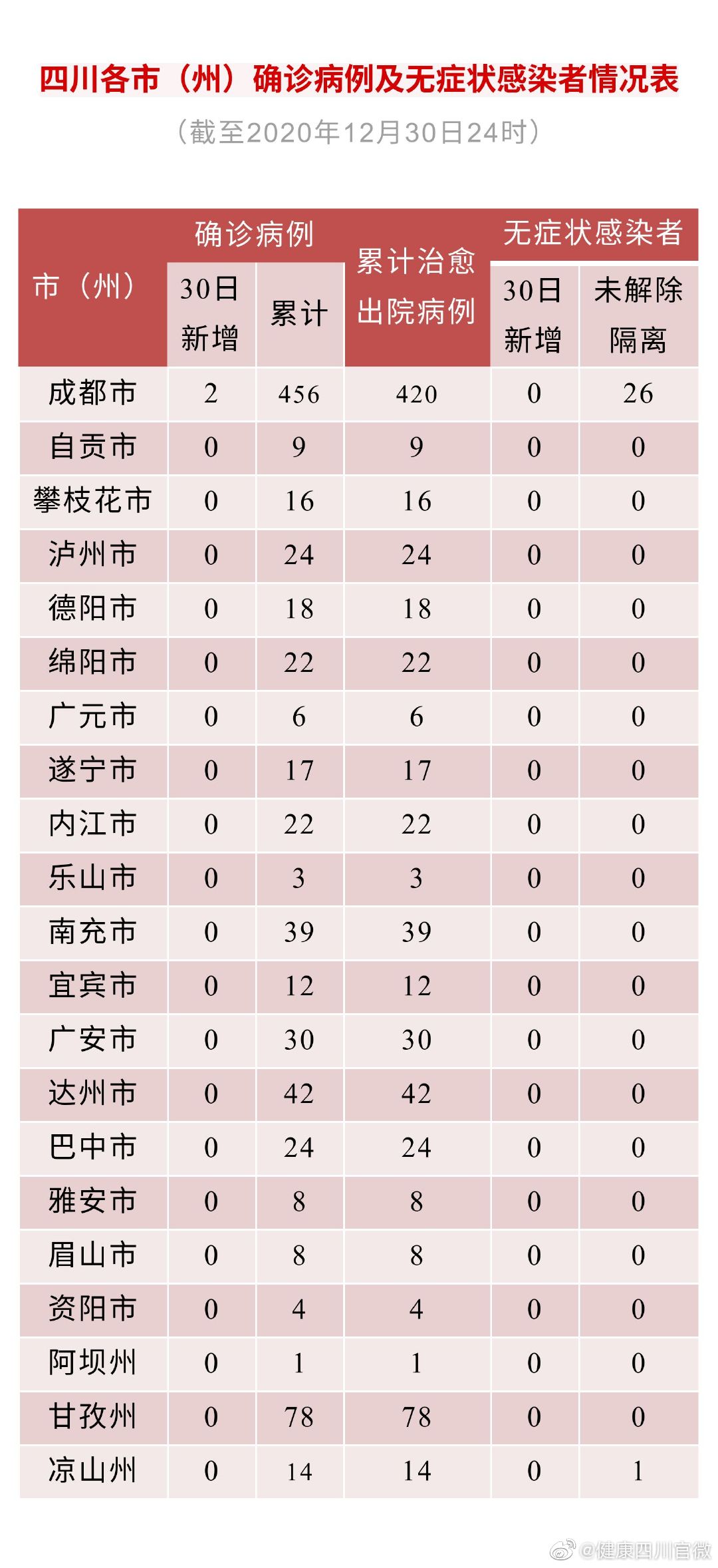原标题:【专访乔姆斯基(下)】人类若多一点闲暇,世界将会怎样?

乔姆斯基。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王磬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刚刚度过了他的92岁生日。
新冠肆虐全球,他所在的美国亚利桑那州是重灾区。作为高危人群的他自打3月份起便闭门不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通过网络继续工作——教课、接受采访、参加会议、发表演讲。病毒没有打断他工作的节奏,年龄也没有。
过去七十年的生涯中,他最重要的职业身份有两个:一个是语言学泰斗。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已经凭借着《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他,如今仍然每周都在网上给学生授课。另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从上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活动开始,他几乎从不缺席重大公共事件,是“永远的异见者”。他所到之处,鲜花与臭鸡蛋齐飞。爱戴他的人称他为“美国的道德良心”,厌恶他的人则向他发送不计其数的死亡威胁。
1928年,乔姆斯基于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萧条伴随了他的童年。10岁时他便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警告纳粹军国主义向欧陆扩散的危险。60年代开始,他积极投身到反越战的活动中,甚至险些入狱。70年代,他与法国思想家福柯开展了一场关于人性的辩论,至今仍被视为世纪经典。他著作等身,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的研究被引用的次数排名第8。除了专业语言学,他还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揭示权力运作,尤其擅长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批判。他不迎合权力、也不迎合民意。即使是在举国悲痛的911之后,他仍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关于他的人生故事和学术思想被多次拍成纪录片。90年代,《纽约时报》称他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维系至今仍无人超越。身边朋友评价他,八九十岁的躯体里仍保有二三十岁年轻人的热情,永远愤怒,永远不合时宜。
在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界面新闻连线专访了乔姆斯基,谈及了新冠疫情、全球威胁、美国大选、中美关系、人工智能和知识分子责任等多个议题。
以下是访谈实录的下半部分。刊发时有编辑。
界面新闻:我想接着问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关的问题。您有许多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其中一个层面是技术发展以及它对未来工作方式的可能影响。在人工智能等领域获得的技术迭代将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也有人指出,它可能会令人类劳动者逐渐被机器人取代,至少在某些领域,失去工作的人将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同时失去罢工的机会。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者在未来的关系?失去了劳动者身份的人们将如何继续保有声音被听见的可能性?
乔姆斯基:看看我们面前的真实世界。大量工作仍需由人力完成,哪怕是最具科幻小说色彩的那一类机器人也永远不能替代:健康护理、教学、服务岗位、研究、建造… …这些都得靠人力完成。目前还没有人敢放心派一个机器人去医院伺候临终病人喝水……这还是健康护理吗?这是病人真正需要的吗?替代一说就是异想天开。真相是,仍有无数的工作需要人类去完成。这些工作的报酬可以很丰厚,可以是充实的,你可以做好事并且乐在其中,你也能控制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服务于某个主人。你的工作并非琐碎且机械重复的,如在亚马逊仓库里往来于两个地点之间,或者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要是机器人能完全代替人干这种活,那就太美妙了。人类就不用做那些愚蠢、无聊或危险的工作了,就能解放出来去做那些充实的、富有创意且必要的工作。
在一个体面的社会,这些可能性是向我们敞开的。如果人们对你所描述的景象忧心忡忡,那是因为社会本身的病态。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一个病态的社会提升为体面而人道的社会。令人反感、有害或危险的职业如果能一律自动化,那再好不过。人类可做的事还有很多——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人类要是能多一点闲暇,世界将会怎样?那是一种犯罪吗?比如,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勤于工作。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普遍比欧洲人长4-6周。欧洲人有母亲产假,某些国家甚至父母都能休产假,在美国则不然。欧洲人因此比美国人更糟糕吗?我不这么看。那是非常美好的。
如果人们能有足够的闲暇,那就能追随自己的兴趣和关切。人们也许会在自家车库里修车,也许做研究,也许在食品贮藏室里帮忙… …总之大家有了做这些事的自由,“工作”这个词届时会比现在悦耳得多,而不再只是急匆匆地为老板给你规定的业绩而奔命。
界面新闻:说到欧洲,英国即将正式退出欧盟,这曾被视为欧盟一体化遭遇的重大挫折。您认为欧盟的未来将会是继续加深一体化进程、还是会走向反面?
乔姆斯基:这取决于我们。凭空揣测没有任何意义。这是行动的问题,而非玄谈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
界面新闻:让我们回到美国。我很好奇您对拜登治下中美关系走向的观察。如果说,可能存在一个修复中美关系、化解某些问题的机会窗口,您认为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才是对于全世界有利的?
乔姆斯基:拜登和民主党的对华立场与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基本一致。某些方面甚至还更为强硬。我认为这很危险,是极具自毁性的政策。对美国人以及全世界都不利。
中国当然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也有一些做得不错的地方。例如,作为大国比较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电气化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以新冠疫情为例。一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各国都在快马加鞭研发疫苗。但在美国却有些不太好谈及的地方。大家热情如潮地谈论疫苗,但却忘了一件事:中国的疫苗。这甚至都没法提。一谈到中国,基本都是负面消息,别的都不方便提。但中国已经生产了疫苗,并已经投入使用。据说,它们的有效性在90%左右。不久前我曾与一名顶尖的巴西生物学家聊天,他们正迫切地想得到中国的疫苗。他们认为该疫苗相当有效,比起辉瑞、牛津和Moderna的疫苗还有很大优势:储存便利,放在普通冰箱的冷冻室即可,不需要特殊的器材。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进入缺乏高科技设施的贫困乡村地区,这一点非常关键。
但在美国基本不提,因为“中国”这个词在那里。哪怕它将有助于美国人,也是不便声张的。这种宣传系统十分惊人,强大到不需要借助暴力。此外,疫苗的有效性被验证之后,怎么分发也是个问题,能不能分好还是个未知数。中国至少宣布愿意向穷国提供几乎是免费的疫苗,产量也达到了上亿支的水平。
西方在做些什么?为富国垄断疫苗。目前最糟糕的例子是加拿大,它还自诩是高度人道的社会。这次加拿大订购了比实际可能的用量多得多的疫苗。但穷国却两手空空。其它西方国家做得已经够差了,但加拿大是最恶劣的。美国和欧盟也在干类似的事情。与之相反,中国却宣布要向穷国分发疫苗。
不过,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当务之急是中美、中西必须在共同关切的领域、为共同关心的公共利益而通力合作。但这不等于说,双方需要因此停止对对方做错的事情闭嘴。谴责仍是必要的。因此,保持批评,尝试改变,与此同时,通力合作。
这个原则对于我们共同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成立。疫情没有国界,它是国际性的: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否则绝无可能取胜。全球变暖也一样:不会停在国界线上。如果美国打算增加排放,全世界都要受害。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减排目标——即在未来三四十年内实现零排放,那全世界都将受益。核战争就不用多说了。如果有两个大国相互打核战,那全人类都完了,不管你在哪里躲藏都是没用的。同理,民主的衰退也是一样,它具有扩散性,和病毒一样。如果民主在美国衰落了,其它国家也会受影响,譬如巴西,继而波及全球。鉴于此,我们要意识到挑战的广泛性和严峻性,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通力合作。
界面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与您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终其一生,您都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针砭时弊,讲述真相,揭示权力,这鼓舞了全球各地无数的年轻人,也包括我自己。如今的世界正在剧烈变动,在您看来,对当今的知识分子而言,哪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哪些东西将永远不变?
乔姆斯基:知识分子之本从来就体现在其所承担的责任之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虽然相对现代,但类似的人和事在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始终有人在探询、追问、帮助他人打破陈规陋俗,使他们能为自己而思考;还要授人以渔,让他人学会在两难面前做出抉择,到达更好的世界。
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腊时期。有一个年轻人被迫饮鸩而死(编者注:指苏格拉底),仅仅因为他善于提问,让年轻人去思考而非被动接受,就被指控腐蚀雅典青年心灵。与此同时,圣经记载中也提到了名为先知(prophets)的人。但他们其实不是先知,而就是我们如今所称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批判了暴君的恶行,呼吁善待寡妇和孤儿,并通过地缘政治分析指出国王正在把国民带入灾难。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入狱,被流放到沙漠里,被污言秽语辱骂。而当时受到尊崇的阿谀奉承者,在几个世纪以后则被贬为假弟兄。历史最终还他们以公道。
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带着现代的含义而被引入的。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Dreyfus trial)当中,知识分子就是类似于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这样的人。他谴责了国家、军方和司法部门犯下的罪行,后果就是铺天盖地的责难,左拉不得不逃命。法兰西学院的“不朽者们”(immortals)对敢于批评这一建制的作家和艺术家大加告发。今天,我们尊崇当时为德雷福斯发声的人们;但那时他们并非被友善对待。
从古到今,这些道理都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你在西方持不同意见,那只是会被边缘化,可能会丢掉工作,但你不至于被扔到古拉格。因此西方的知识分子责任更大。你若沉默不语,罪责就更严重,因为你的发声机会要多得多。这就是知识分子颠扑不破的天职,放到也今天丝毫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