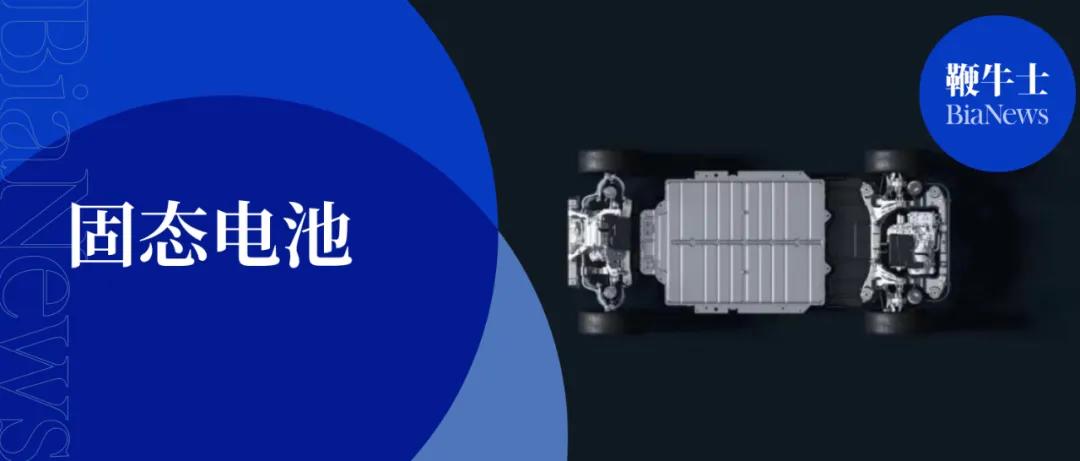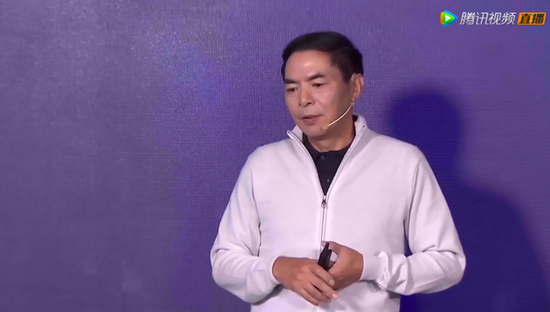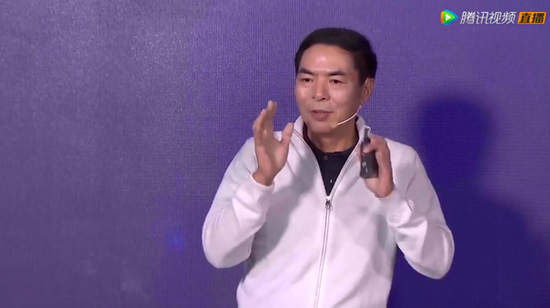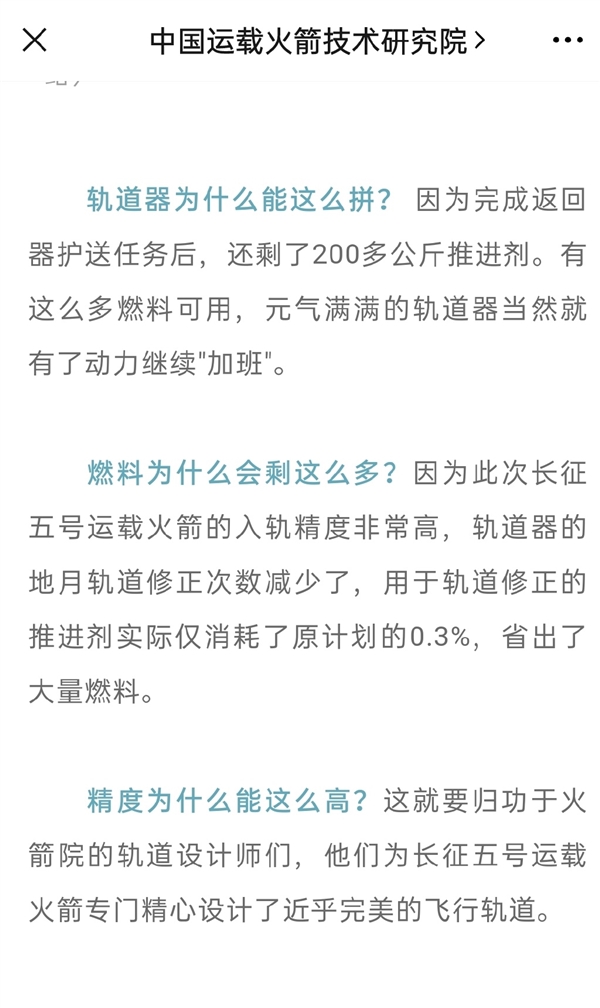来源:第一财经

本文字数:3923,阅读时长大约6.5分钟
导读:当一个独立自主甚至很强势的的现代女性说要冻卵、找代孕,她背后的逻辑就是现代世界的商业逻辑,这里隐藏着一个大众都相信的原则:公平交易。
作者 | 第一财经孙行之
娱乐圈顶流女明星郑爽的“代孕弃养”风波,令“代孕”这个被讨论了多年的问题再次被推向舆论风口。
在美产子,代孕,弃养,前男友,每一个关键词都足以刺激大众的神经,而当这些问题发生在一个争议不断的娱乐明星身上时,舆论被彻底引爆。
对这个话题持久不熄的争论本身就说明,代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或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广泛讨论空间的话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性别研究学者马姝所说:“代孕衍生出的问题很多,并且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和缠绕在一起,很难单独就某一个问题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是需要从道德、伦理、法律、科技、医学等多个维度去透视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广泛探讨。”
马姝还提醒,代孕问题关系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何改善一些女性的生活,改变对她们不利的社会结构,是代孕所提出来的需要我们长久关注的社会议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念也认为,人们应该关注的,是具体的女性处境和女性经验,并以此激活更为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
一度蓬勃发展的地下代孕产业正在进一步击穿私人与公众、生产和生殖、家庭与市场、商业与伦理的界限,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往的习俗、道德、伦理与法律框架的由来和问题。
女性主义倡导“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在代孕问题上成立吗?代孕是否加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当金钱面对生命,它的边界在那里?人们何以能够理直气壮地把生育化为一种交易?正视代孕后果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顾及少数人的权利?
第一财经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张念。
“我的身体我做主”第一财经:代孕涉及到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问题。有人说,“我的身体我做主”,既然可以堕胎,那么对孕母来说,也应该被允许代孕。你怎么看?
张念:从刚性的逻辑推演上,当然“我的身体我做主”。但是这个刚性原则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世界,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当然我们在说一个女性是否具有自主性的时候,要考虑她是否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个体,个体处境如何,精神意识状况如何。但我也反对一切都用经济原因去分析,因为用经济原因来分析太简单了。我们要想想,如果我真的是缺钱,那么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她为什么选择了去出租自己的子宫?
第一财经:孕母通常来自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贫困女性没有赚钱的机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结构没有给她们赚钱的空间。如果有其他出卖劳力的机会,她们不一定这样选择。
张念:你这样的反驳不成立。我们不能泛泛地说,社会没有给他们赚钱的机会,因为劳动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劳动权利和女人工作的权利并不是阻拦,在现代社会也不是障碍。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有没有从女性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彼此交叉和渗透角度去关注这个人群?
如果我们假设是因为经济困顿,也没有非常高的技能,可以做保姆。可为什么有的女性选择了做保姆、有的女性选择了性工作,有的女性选择了出租子宫?我们关心的是出租子宫的这部分人的想法。
出租子宫和性工作,牵涉到女性主义很关心的、关于“女人的身体”的问题。这和保姆不一样,保姆是一个独立的劳动力,是经济学中确认的可计量的对象,所有生产都牵涉到出卖劳动力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被现代社会确认,并且被包装成“正当的”。而一牵涉到女性的身体,我们就变得伦理上态度模糊和充满歧义。这是女性身体存在于世界的另一项作用,它折射出我们既有知识概念的局限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共同面对这一个充满歧义的问题,因此它要求我们的伦理判断应该有新的发明。
现在,我不可能给你一个判断,我支持代孕,或者我不支持。当我们支持代孕的时候,我们就要设定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本身是值得质疑的,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我们进一步能做的就是,通过女性处境、女性经验激发出更广泛和更活跃的公共讨论,我们只能做这件事情。因为在这方面,大量的女性经验和女人的处境一直是被默默压制的,被“理性”的公共舆论视为是“婆婆妈妈的事情”。
当我说我支持,前提就是我认同这个刚性的逻辑推演,“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也是西方女性主义两百年发展提炼的女性解放的原则。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女性主义内部也有争议,比如,性工作合法化是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代孕折射出的性别平等现状第一财经:谈到男性中心主义,这里有一个与“男女平等”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谈到代孕的时候,看上去似乎是夫妻更为平等了。近代以前,男性以一夫多妻的方式更多的繁衍后代。现在,妻子从生育这件事上解放了出来,“外包”给市场,这个任务可能由世界另一个角落的、相对贫苦的女性承担下来。这样说来,代孕是把夫妻不平等的问题转化成经济和阶层不平等了。对富裕女性而言是更大的解脱,对贫苦女性则构成了双重压迫。
张念:如果从单纯的阶级或者阶层的划分,说这是有钱阶层对贫苦阶层的压迫和剥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枯燥解读。如果我们抛开理论,进入这些女性具体的处境,当一个婚姻共同体面对一个相对贫苦的女性,她们没有知识、没有金钱,只能选择出租身体的时候,婚姻共同体的诉求是什么,就是生育。
那就是说,进入婚姻的这个女性也接受,生育是这桩婚姻的第一要务。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女性的观念是自发的吗?更何况想要一个孩子 ,成为母亲,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在女人这里,终究要被体验为身体的、心理的或意识的经验。
第一财经:不同的女性动机当然有区别。有一些富裕家庭,因为长辈或者丈夫希望多生育、甚至单纯是想要生儿子而选择代孕。但也有一些女性,比如一位“新时代女性”演员,就曾在一档谈话类节目里提到,自己已经冰冻卵子,并坦然地说,今后如果要生育,那就是找人代孕。这整个过程并不一定需要进入婚姻。看上去,这似乎是她独立的、自发的,是一种反叛父权制的行为,和第一种情况不同。
张念:的确是存在两种情况,前一种是男权中心文化。但那些宣传独立的女性,她的自主性也是很可疑的。我可以选择什么,或者不选择什么就是自由?这是我们对自由的最大误解。分析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当她说冻卵、找代孕,她背后的逻辑就是现代世界的商业逻辑。这个商业逻辑隐藏着一个我们都相信的原则:“公平交易”。
面对生命,金钱的边界在哪里?第一财经:你说的这种“商业逻辑”对人的异化是比较严重的。当一位手握丰厚资源的女明星一边标榜自己的独立自主,一边却对征用另一个女性的身体没有多少犹豫的时候,这里头的道德紧张感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为代孕付出的钱足以改善孕母家庭的生活,因此还可能是站在公平交易、甚至施舍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张念:是的。这种商业逻辑很可怕。单纯凭借一种商业逻辑告诉我们的“公平性”,就可以放弃伦理和道德上的犹疑让自己心安理得。良心这个事情是天性,但我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抚平良心的不安,这个借口就是被现代社会建构的、通用的“公平交易”原则。
而那些解放了的、独立的现代女性在面对商业逻辑的时候,可以毫无犹疑地接受这件事,她依然是男权主义的。商业逻辑的男权逻辑背后就是女性主义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逻辑之下的男权中心主义,更不要说现代社会的整个建制体系都是男权逻辑的。他们蔑视、忽视人的复杂性、人的意识、心理和伦理感受,这些都是被压制的。
第一种情况是明显的男权主义的,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伪装的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因为不符合女性主义200年来的原则:那就是,女性对处境意识和伦理感受更为敏感。女性经验所富有的这种敏感就被商业逻辑所排斥和清除了。
代孕的问题牵涉了我们生活世界和有限生命方方面面的问题,渗透性和延展性很强。媒体就是要倡导一种活跃的有延展性的公共讨论空间。我们可以探讨传统习俗和商业逻辑背后的理性框架有什么不足。
反对呼声下不孕人群的境遇第一财经:这两天,因为郑爽的新闻,网上反对代孕合法化的呼声很高。代孕一开始可能是互助和善意驱动的,解决了一部人的现实困境。至今,在印度和美国的代孕机构,依然有这样的话语,认为孕母是为母亲带来天赐礼物的使者,他们是施助者与受助者的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无法自己生育的少数人的诉求是不是也应该被考虑到?
张念:我没有考察过代孕起源,但起点也许是我们的生殖科学技术可以做到了。我们可以参照的是,在辅助生殖技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西方人怎么解决?他们的价值是,必须维护私有财产的恒久性,那就必须要继承人。少部分人如果绝后,他们就用个人基金或者委托人制度,或者是委托在某个基金会。财产最后归于社会。有了技术以后,少数人的确有权使用代孕这种方式。
在传统中国,我们是宗法社会,因为要维护一个家族和宗族的恒久昌盛,我们会选择过继。每个时代,绝对需求的排序是不一样的。现代人活得很混乱。没有辅助生殖技术以前,中西方社会的选择背后有一套价值排序,我说的是价值,而不是需求,因为人是贪婪的,需求是漫无边际的。我们现代人既没有共通财富(common wealth,中古英语中还有国家的意思)、公共诉求,也没有基于家族血脉的宗法共同体价值诉求,你仅仅凭借一己私利来呼吁少数人的权利,这是很可疑的。人是很任性的,偏好是随时会变的。那我要问你,你要个孩子背后的公共价值诉求是什么?
第一财经:就当下而言,很多人的生育动机,可能和公共价值无关,而更多是出于情感寄托。
张念:对,情感价值。如果是情感价值,很多人可能会去领养。这可能是出于宗教信仰,这种价值并不是施恩,而是有神在天上看着我,看着我干了些什么,这背后有一套宗教语言系统。我们现代人有钱,但是活得很可怜。什么是情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