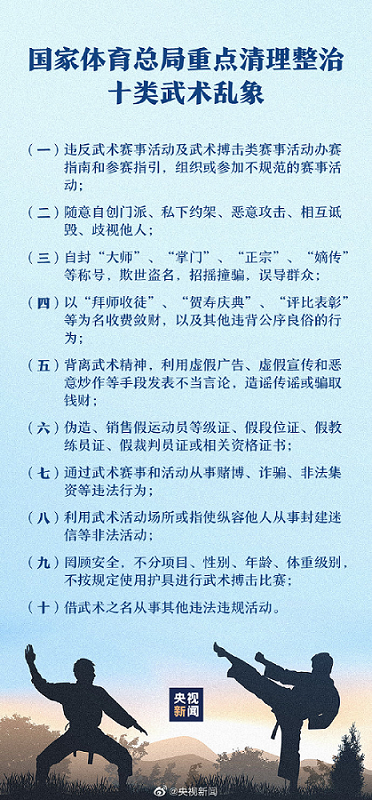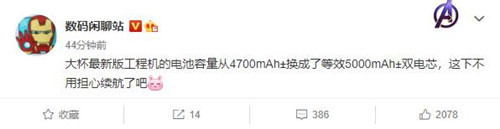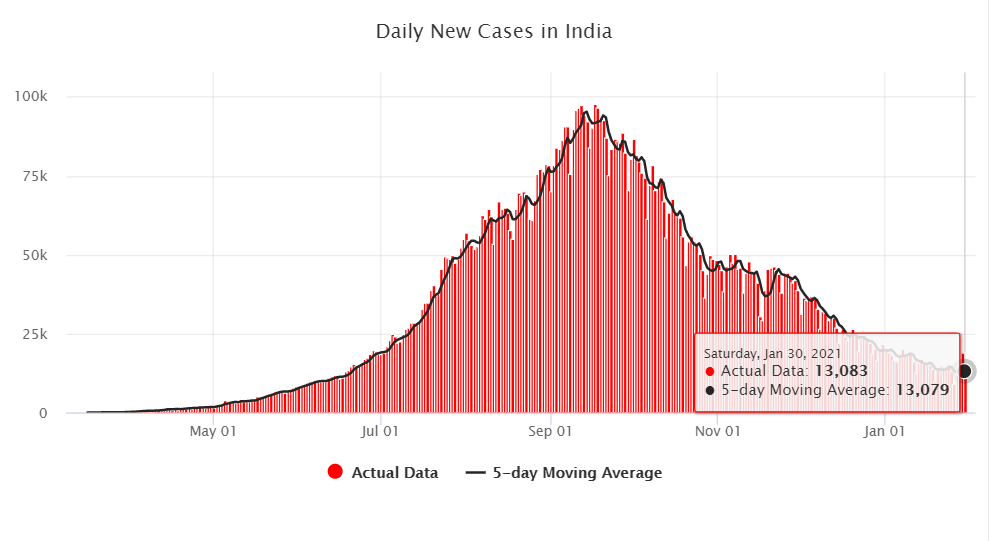原标题:李铁:土地红利仍在,如何通过改革寻找新增长点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是一个老话题,其实中国一直在经历着农地经营制度的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再到允许农地流转。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在农地改革道路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
另外一个重要的土地改革领域涉及城乡用地关系,中国曾经放松了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从而释放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兴办乡镇企业的巨大潜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沿海地区县域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
但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受到严格的管制,从而严重限制其参与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来。
这种限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确保城市能低价用地,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不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开发市场,以便于低价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二是出于耕地保护的需要。中国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通过下达年度计划安排农村土地开发和征用,避免各级政府滥占耕地,同时防止集体经济组织过度开发农业用地。三是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目标出发,防止“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农村生态破坏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四是防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房地产,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五是城市规划的约束和限制,避免因农村集体土地的自行开发,形成低水平的居住空间,影响城市形象,并增加未来城市开发时所产生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成本等等。
通过低成本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来获取城市发展用地,是中国独创的城市化道路。当下,在传统体制优势逐渐丧失的形势下,如何借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找到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值得研究和思考。
传统土地红利正在丧失
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之一就是土地红利。很多人认为,中国增长的动力源是人口红利,但要看到,人力资源同样十分丰富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中国长期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这些国家无法解决城市建设用地涉及的征用和开发成本问题。而在中国,不仅在工业化进程中,而且在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过程中,都充分发挥了土地低成本的优势。没有土地制度的红利,中国的城市不会发展到今天如此的规模。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现有体制下土地红利优势已在逐步丧失。依托于房地产开发和土地出让金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工业化进程,也因土地开发成本的上升而呈现不可持续的态势。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深入贯彻和落实,中国通过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继续补偿工业和城市建设开发成本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分享工业和城市开发收益,也因此抬高了土地出让价格。
目前,中国耕地保护任务仍十分艰巨。目前的耕地保有量无法满足14亿人口的农产品需求。虽然现有20亿亩耕地可以提供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但是从品种调剂和多元化农产品供给,以及进出口贸易平衡方面,还要通过国际市场对一些大宗农产品供给进行补充。
目前中国进口的各类农产品已经超过1亿吨,如果算上肉类、奶制品以及其他农产品的进口量,相当于中国在国外至少占用了10亿亩耕地,几乎相当于中国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从稳定和保障的大局出发,无论是在丰收或欠收年,维持主要农产品的供应应该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要求。仅从这一点,放松对耕地的严格管制,不是未来政策的选项。
从1997年开始,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针对农村乡镇企业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现状,关闭了全国县以下的工业开发区。
政策的出发点一方面是防止乡村各自为战,盲目发展工业,滥占土地无法遏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乡镇工业布局过于分散,无法监管,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污染。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县以上的工业园区呈现出等级化的特征。等级越高的城市,园区集中度越高,相应的征地成本也高。虽然乡村大规模发展工业企业的状况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但是因为没有更多土地供应以及制度跟进,无论是城市开发,还是工业园区的兴办,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成本攀升的问题。因此如果要让新的低成本开发空间进入到工业和城市领域,就需要在相关管理制度上进行改革和调整。
从限制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的政策出发点来看,还有一层担心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对开发有过度热情,如果不采取严格的政策限制,那么农民为了获得短期收益,将再也不会热衷于种地,而是热衷于“种房子”。
通过改革释放土地新潜力
目前中国仍然面临着破解现行土地制度的困境。例如,在一些特大城市的郊区,很多城市居民愿意到郊区农村租赁和购买住房。
一旦这个口子放开,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状况:一是会出现村村热衷发展房地产,严重冲击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二是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三是由于分散建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过于分散,无法集中布局而形成规模收益;四是即便有严格监管和限制,仍然阻挡不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与城市居民租赁交易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由于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一旦发生纠纷,对交易双方都可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显然,有序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改革,仍然是当前改革需要考虑的重点。
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规划如何规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上世纪80年代的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重点都是要确保以低成本的方式维持城市的运转和建设。
这一制度的好处是,促进了当前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实现了城市高速发展和建设。另外一面是,遏制了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活力,同时以房地产发展支持产业园区的模式,无论是新区,还是园区,都经历了开发成本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
另一类问题是以房地产开发推进城市建设,以及通过规划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导致城市周边农村建筑形态缺乏个性化特征,也影响了农民从土地入市中可能获得的财产性收益。
例如,对农村宅基地建房的限制,出发点是担心会抬高未来可能的拆迁成本。“大一统”的乡村规划,也因此步入城市规划的窠臼,使得“千城一面”延伸至“千村一面”。另外,在村庄改造中过多地希望通过急功近利的规划,彻底按照城市模式进行拆迁和征地,忽视了在集体土地入市过程中可能实现的产业自我选择和建筑多元化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拆迁补偿收入大大低于改造后或发展产业得到的收入,使他们忽视了一点,利用宅基地住房发展各种经营模式,可以使他们的财产性收益更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一个争议焦点,是回归到传统的土地私有化模式,还是在充分利用集体公有制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有序利用市场机制,释放农村集体土地的潜力和活力。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取得的成功不在于按图索骥的按一种理论或所谓西方模式进行改革,而是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以不破坏稳定发展为前提,通过适度的体制变革释放潜力和活力。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在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方面,许多当年顾忌的矛盾和利益问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城市低成本发展的路径已经遇到严峻挑战。如果不通过房地产开发,对农民的高额征地补偿成本几乎无法兑现。
二是耕地保护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还在不断增加。从2010年到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1亿多人的同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反而增加了2万平方公里。
三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问题在1997年全国清理县以下工业园区之后,已经得到根本解决。而随着土地征用成本上涨的大趋势,规模化的工业企业将从园区集中布局的高成本模式,部分转化为向分散布局的低成本模式。同时,当前环境和生态的监管体系已经十分完善。
四是对房地产开发的各种限制完全可以通过规划和管理强度来约束,与此同时,大量闲置的农村宅基地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如果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投资,或者经营非农产业,那可以把农村宅基地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进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发挥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周边的巨大的潜力。
五是以现有的建制镇区为基础,在人口达到三五万人口以上的小城市,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规划相应的产业和居住区,在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周边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这对于缓解中心城市主城区房价过高的压力,降低产业发展成本,解决外来务工就业人口的居住问题等,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小城市自身的改造和发展过程中,是采取统一拆迁和整体规划的模式,还是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个性化的规划和建设模式,还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不是为了所谓的某种模式而去强制推行。而是要在尊重中国国情和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减少利益冲突,更多地释放改革的潜力。
在城乡利益格局相对固化的形势下,考虑如何绕开那些易引发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回避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更多从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入手,着重通过空间格局的调整,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本,从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居住和就业问题出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其他相关体制性变革都还有很大的潜力可释放。
这也是现在中国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内外部形势变化,可以打出的一副好牌。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
财经号所发布文章之版权属作者本人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财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