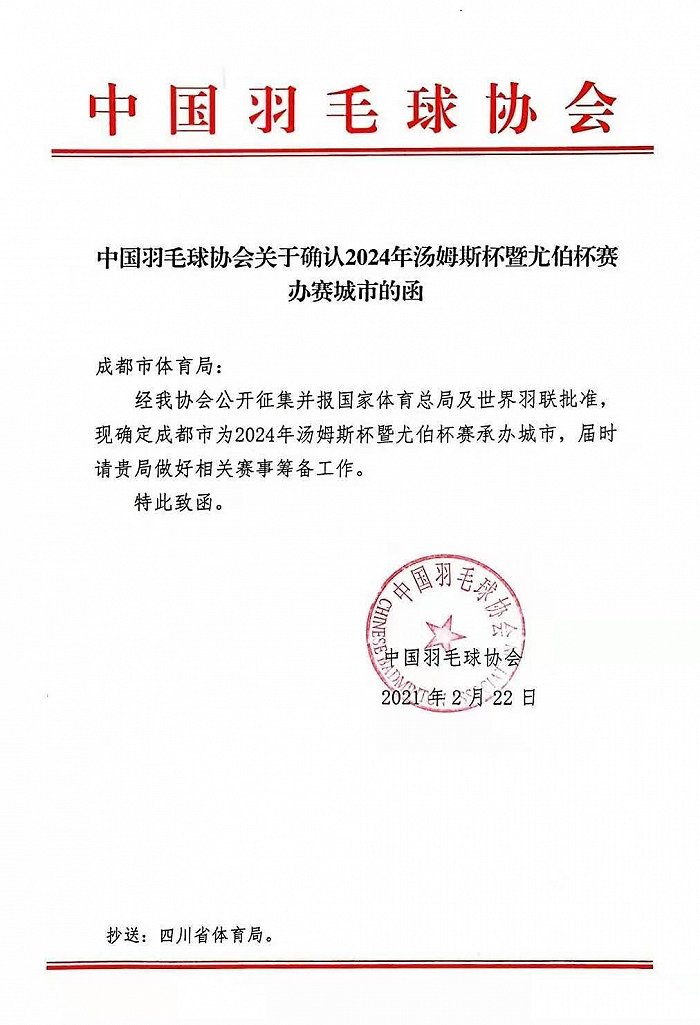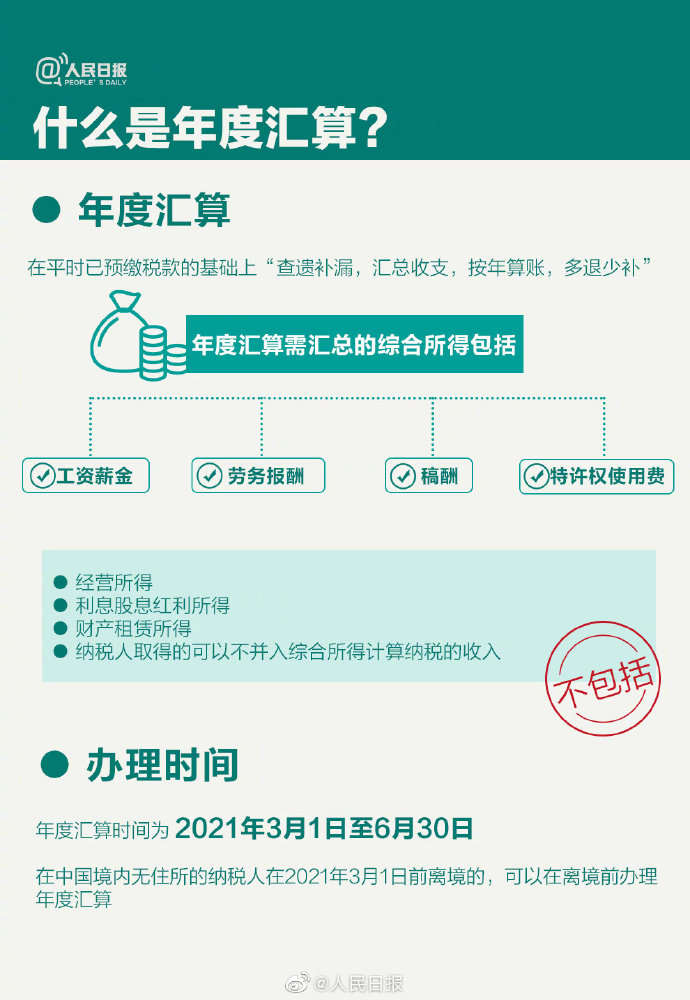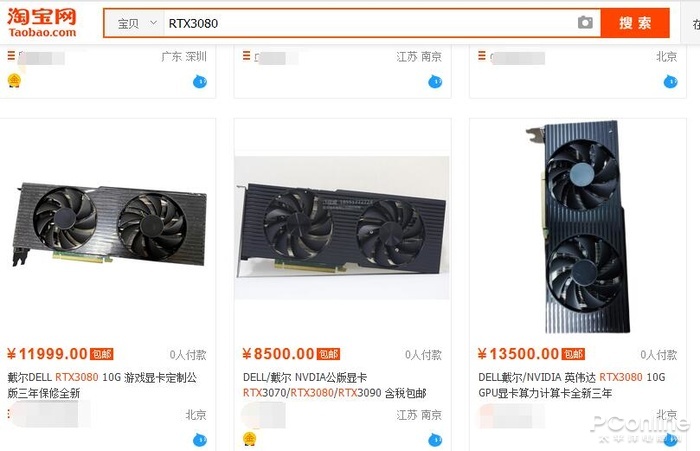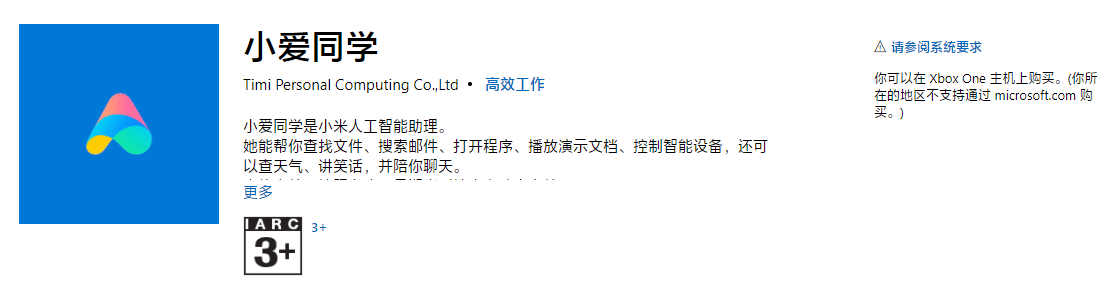原标题:季卫东:风险社会与法律决策的概率计算

完全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偶然、无知以及出乎意料;风险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但以发生的盖然性为本质特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进行把握,即可以对风险进行预期值的计算。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季卫东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深入探讨了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状况下的法律决策。
最近三十几年来,社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主要的缘起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出版。中国公开讨论风险社会问题仅有十年左右,但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使这些问题再次显现出来。
日常生活中谈论的风险,指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状况。但从学术上来看,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概念进行区分。完全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偶然、无知以及出乎意料;风险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但以发生的盖然性为本质特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来进行把握,即可以对风险进行预期值的计算。风险所造成的危害与预测是否准确、防范举措是否及时和适当相关,因此对风险的管理可以追究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确定的社会中,预防与规制的举措,也可能会引起新型风险或者潜在风险。比如,对新冠病毒采取的隔离决策,防治效果非常明显,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度防范的问题?比如,过于严格的隔离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上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有可能使得其他的疾病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大家都进行疫情的防控,不敢也不能去医院对其他疾病进行诊断。这时可能产生另一种风险:因新冠病毒感染而产生的患者人数或者致死率下降了,但是因其他疾病而产生的患者人数或者致死率可能反倒增大了。这些就是潜在风险,或者新型风险。
对于政府而言,采取预防和规制措施的费用相对确定,但是风险的收益却不确定,这会导致政府在防疫措施方面处于犹豫状态。欧美许多国家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举措决策就是很好的实例。由于其相关制度对规制措施的费用限制,政府很难断然采取隔离措施;发病率、致死率的高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防疫措施的收益也看不清楚,因而美国围绕新冠疫情防控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对立,相关政策争论也成为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焦点。
此外,社会各方在风险评估方面的想法也非常不一致。专家更关注损失的概率和数额,群众更关注损失、痛苦以及风险分配的公平性。而大众传媒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实际危险的忽视具有不均等性和非对称性。如果大众传媒以及网络舆论对于某些特殊的危害特别关注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导致主观危险先行的状况,造成紧张气氛。特别是,在风险沟通过程中还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比如价值观比较一致的人一起讨论问题,会就某一现象发表类似意见,这种意见反复交织积累,就会形成共振或共鸣,最后导致原有价值取向越来越鲜明甚至越来越极端化。
决策和司法判断都应该考虑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将概率的计算纳入风险治理的视野之中。一般而言,概率计算的概念存在4种类型。第一、二种是算术概率和统计概率,均为频度解释;第三种是公理概率,从公理出发并通过概率的计算最终找出事物演变的倾向;第四种是主观概率,根据既有经验、知识和信息做出可能性判断,此时对概率的解释是主观的。在涉及法律决策和司法的场合,经常使用的是主观概率。贝叶斯定理及其推定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主观概率的计算类型,跟法律判断密切相关。首先,法官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并结合现在获得的信息,提出一个先验概率或假说,即法官的内心确信;其次,根据假说来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一般来说就是数据);再者,求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概率,即条件概率;最后,根据所得数据来验证假说,此时得出的判断就是后验概率。

社会的不确定性状况也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从概率论的角度对与不确定性状况相关的概念进行区分,大致可表述为确定性、风险、真正的不确定性、预想之外的不确定性和无知五种。如果已知的某一事物确实已经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那事物就是确定性的;在复数的事物当中,某一事物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虽然不知道它具体情况是不是发生了,但是知道各种事故发生的概率,这就是风险;在复数的事物中,不知道哪一事物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也不知道各种事物发生的概率,那就是真正的不确定性;如果无法列举所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话,那就是预想之外的不确定性;如果完全不知道哪一事物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那就是无知。
经济学曾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状况下的决策进行过非常精彩的分析,这对法律问题的解决也极具参考价值。例如,弗兰克·奈特在关于目的和复数的手段选项分析中指出,在对一个目的存在复数的手段选项的情况下,找出一个最优手段或最优解决方案,当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时,很难进行选择。对此,奈特在经济决策方面提出了满足度标准、最低限度最佳标准、后悔最小化标准等建议。在风险状况下的决策面对盖然性,还可以根据一个期待值来进行判断。比如买房、炒股的行为方式是买涨不买跌,结果很容易悔不当初或者不敢出手,这时他人往往会劝其不要老是后悔和对比,也别说那时候如果买了就好了的话,只能大致确定一个期待值,按照这个期待值来计算盈亏。
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状况下的法律决策,也需要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针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一些传统制度设计很有意思。例如罗纳德·德沃金的司法裁定论主张审判者要寻找一个正确的解答,甚至是唯一的正解。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司法的话语中缺乏这样的观念,《名公书判清明集》里反复出现的论题是如何通过商谈或调解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让当事人各方都满意,避免依法判决造成的后悔。奈特经济学提示的最低限度最佳标准、满足度标准以及后悔最小化标准在这里都能找到,似乎中国传统司法总是在进行风险决策。当今法院提出把当事人满意不满意以及人民满意度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也是由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要求司法决策充分考虑政治大局、社会变化、具体情节等等。换言之,如果司法机关必须在一种不确定性的状况下进行决策,那就势必强调比较意义上的更好而不是唯一正确解答、势必强调表现为满意度的社会效果而不仅仅是严格服从法律。提出这些口号、做出这些政策选择的人未必知道奈特的理论框架以及在不确定性中进行经济决策的判断标准,但对两者之间的高度类似性的确饶有兴味。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6期
(作者:北大金融评论 )
声明:本文由21财经客户端“南财号”平台入驻机构(自媒体)发布,不代表21财经客户端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