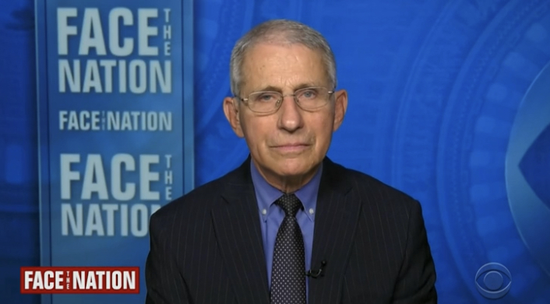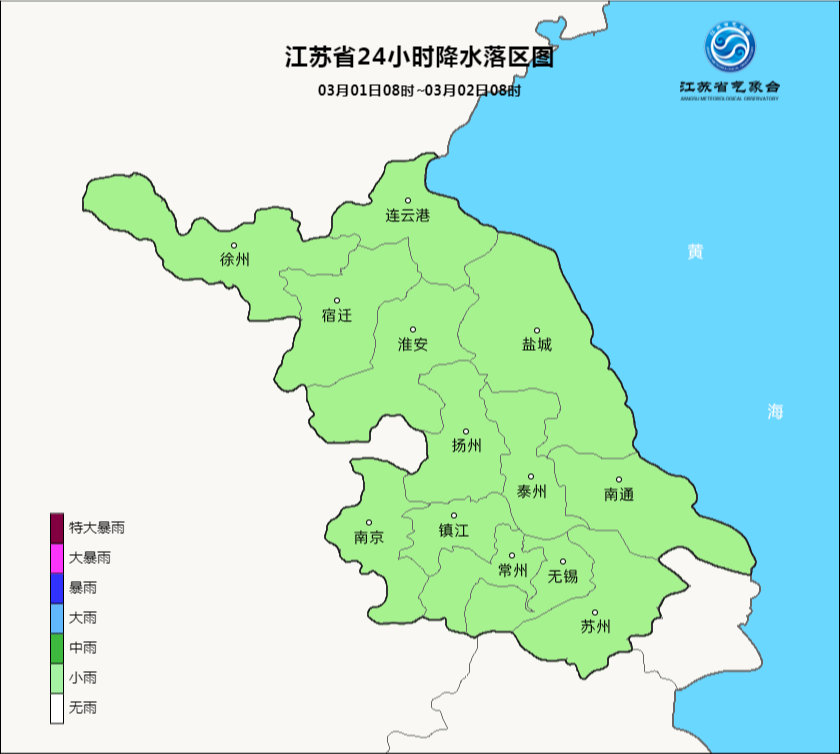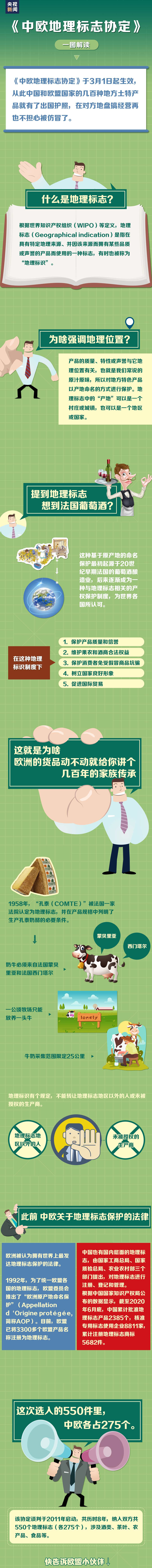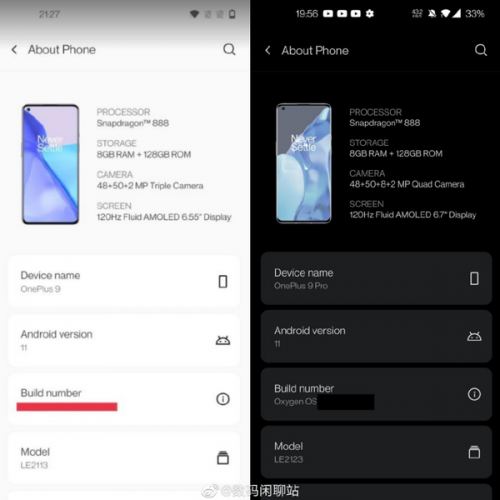原标题:石黑一雄:AI、基因编辑、大数据……我担心我们再也不能控制这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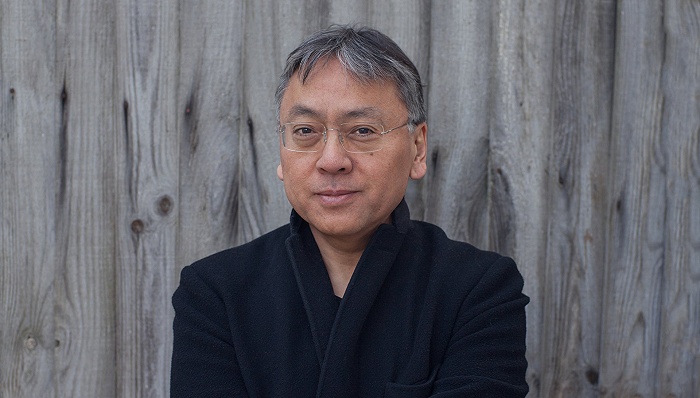 石黑一雄 图片来源:Howard Sooley
石黑一雄 图片来源:Howard Sooley对石黑一雄一家来说,2017年10月5日是个重要的日子。经过数周的犹豫,这位著名作家的妻子洛娜终于决定换个发色。当时她穿好了理发袍,坐在汉普斯特德发廊里——距离他们一家住了很多年的伦敦郊区戈尔德斯格林不远,她瞟了一眼手机,正好看见刚收到的一条新信息。“很抱歉,我不能做头发了,”她对站在一旁等待的美发师说,“我丈夫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许需要我的帮助。”
此刻的石黑一雄正待在家里,他比较晚吃早餐,这时他的经纪人打来了通知他获奖的电话。“诺贝尔奖和布克奖正相反。布克奖通常都会先有一个长名单,然后是短名单,就像是持续轰响的闷雷。而诺奖则简直就是一道毫无征兆的晴天霹雳,突然之间就把你砸中了!”接到电话后不到半小时,石黑一雄家的门外已经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记者。他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说:‘我获得诺贝尔奖了, ’奇怪的是,她似乎并不意外,”石黑一雄回忆道,“当时她说:‘我知道你迟早会获奖的。’” 石黑静子于两年前去世,享年92岁。石黑一雄的最新小说《克拉拉和太阳》(Klara and the Sun)就是献给母亲的,小说的部分内容涉及母性的奉献,也是他获得诺奖后首次推出的作品。 “我能成为一名作家,我的母亲起了很大的作用,”石黑一雄说。
我们通过Zoom进行了本次访谈,他特地躲进了一间空置的卧室里,房间的书架上堆放着女儿娜奥米读本科时的教科书。他说他自己的书房很小,仅仅能放下两张桌子:一张摆放他的电脑,另一张安放了一块写字用的斜板。平时没有人会进他的书房。令我受到鼓舞的是,他借用了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一个场景,把我们这次采访过程比作小说中的一场审讯,那一段解释了间谍如何通过编造一套又一套貌似可信的背景故事,而挺住各种审讯折磨,“直到他们只剩下了一个发出尖叫的脑袋。”不过,采访过程中,他十分乐于接受各种提问,而且实际上,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所谈及的内容都像你在读他的小说时所期待的那样细致入微。
 石黑一雄,凭借《长日将尽》获得布克奖。摄于1989年。图片来源:AP
石黑一雄,凭借《长日将尽》获得布克奖。摄于1989年。图片来源:AP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当时62岁的石黑一雄算得上是一位年轻人。年少有成本来就是石黑一雄神话的一部分:年仅27岁,他已经成为《格兰塔》杂志首次评选的英国最优秀青年小说家名单上最年轻的作家(同时进入该名单的还有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十年后他再次进入了该名单。在此期间,他还凭借《长日将尽》获得了布克奖,这部小说于1993年由墨臣艾禾里电影制作公司改编并搬上了大银幕。石黑一雄曾经放言,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都是作家们在他们二、三十岁时创作出来的,这也确实已经成为了其文学传奇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一直到处说这句话的人是马丁·艾米斯,并不是我,”石黑一雄爽朗地笑着说,“他被这个想法迷住了。”但是石黑一雄仍然认为,30多岁是一位作家创作小说的关键时期,“你的确需要一些特别的脑力。”(在这一点上,28岁的女儿娜奥米十分幸运,本月她将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共同点Common Ground》,她的父亲感到十分欣慰。)每当有人提起有关诺贝尔奖的话题,石黑一雄的标准答复都是“作家们大多都在60多岁时凭借他们30多岁时创作的作品获得诺奖”。“我本人恰好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位现年66岁的作家平静地说。
石黑一雄仍然是自我封闭世界里的超级创造者,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处于某种封闭状态(或者居于乡村别墅,或者困于寄宿学校)。他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细节近乎苛求地关注,加上貌似随意平淡的叙述风格,淡化了他的作品里充满奇幻构思的情节和刻意压制的情感强度。他的新作《克拉拉和太阳》(Klara and the Sun)也不例外。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美国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讲述了(至少表面看来如此)一个人造的机器人“朋友”克拉拉和她十几岁的主人兼监护者乔西之间的关系。在那时,人工智能机器人(AF)已经变得像真空吸尘器一样普遍,基因编辑成为一种常态,生物技术的进步接近于可以再造出独一无二的人类。“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幻想,”石黑一雄说,“我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着什么样的可能。”“亚马逊的推送功能”只是一个开始,“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也许开始有能力重建某些人类的性格特点,这样人们在死后仍然可以继续存在于网络上,大数据能够推算出他们接下来会在网上订购什么东西,他们想去观赏哪一类音乐会,以及在早餐桌上当你给他们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他继续说道。

《克拉拉与太阳》
[英] 石黑一雄 著 宋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04
他刻意不去读伊恩·麦克尤恩最近写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和珍尼特·温特森的新书《弗兰吻斯坦》(Frankissstein)。这两本小说也都是以人工智能为背景,但视角非常不同。克拉拉类似一种陪伴儿童的机器人,“在照顾乔西这件事上,她有着像终结者一样的决心”,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潜在的孩子替代品:当乔西生病时,克拉拉就被改编程序以方便取代乔西的位置。“在这样一个我们改变了对人类个体和个体独特性看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爱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问道,“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关于人类灵魂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听起来总让人感觉空洞浮夸:人类到底有还是没有灵魂?”
石黑一雄的这本新书回顾了他写于2005年的小说《莫失莫忘》里的许多想法,那本书讲述了三名克隆技术生产的青少年的故事,他们身上的器官最终将被摘取,因此他们在30岁前将注定死亡。“这只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轻微夸大,到了某一时刻,我们都将会生病或死亡,”谈起那部小说时石黑一雄说。这两部小说都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真爱可以延缓或战胜死亡,但这种可能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加以检验和证明。这种带有童话意味的对生命的讨价还价,也明确体现在他之前创作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船夫对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就提出过类似的挑战。这种希望,即使对于那些并不相信有来生的人来说,“也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其中一个原因,”他继续反思,“这些想法也许会让我们显得很傻,也许这些不过是大量感情用事的废话,但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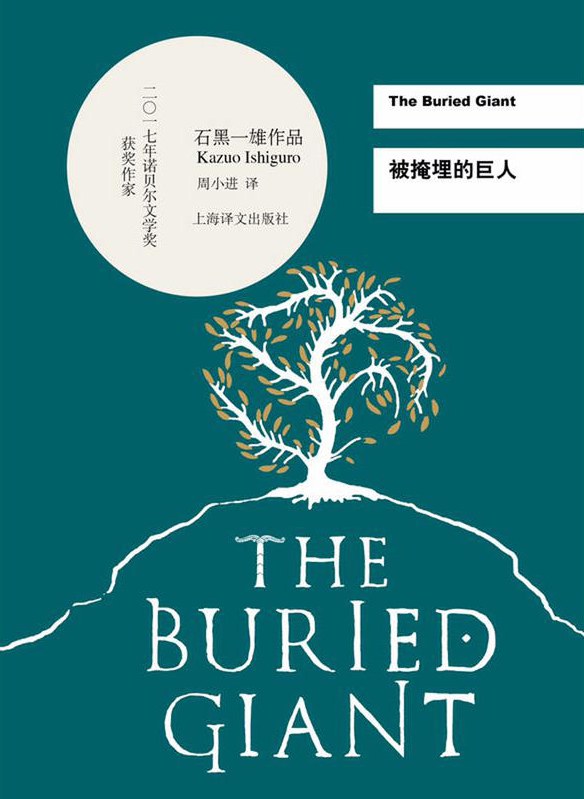
《被掩埋的巨人》
[英] 石黑一雄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01
对于小说创作中的重复,石黑一雄并不感到抱歉,对此问题他引用了伟大电影导演的“连续性”一词(他是一个超级影迷),并且喜欢对外声称他的前三本小说基本上都是对前一本的重新创作。他说:“小说家常会为自己作品中的重复进行辩护。我认为重复是完全合理的:你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最后就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观点。”通过改变故事发生的地点或体裁,他在这方面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太拘泥于小说的字面意思,他们以为我又开始了新的创作。”对他来说,改变写作体裁就如同去新的地点旅行,他确实喜欢转换不同的体裁进行创作:《当我们是孤儿时》是侦探小说,《长日将尽》是历史小说,《无可慰藉》是卡夫卡式的寓言,《莫失莫忘》是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被掩埋的巨人》是托尔金式奇幻小说(托尔金,英国作家,作品包括《霍比特人》《魔戒》等——译注)……现在,正如他的书名《克拉拉与太阳》所暗示的那样,他来到了他所说的“儿童故事乐园”。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读者其实仍然身处于他的“石黑一雄创作园地”之中。
《克拉拉与太阳》改编自石黑一雄在女儿年幼时为她编的一个故事,他原本打算将这部小说作为他进军儿童文学市场的敲门砖。他说:“我构思了这个非常美妙的故事,我想它一定适合用来制作成那些有很多插图的可爱绘本。我把故事讲给娜奥米听,听完后她板着脸看着我说:‘你不能给小孩子讲这样的故事,他们会留下童年阴影。’”因此,最后他决定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给成年人看的书。
人们对石黑一雄作品的反应总是让他有点惊讶,他说:“我真的很吃惊,人们从我的《莫失莫忘》一书中能读到那么多的凄凉。”他收到过一张哈罗德·品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用他标志性的黑色签字笔字迹潦草地写着,“我觉得这本书太可怕了!哈罗德留。”他强调了书中的血腥意味,“但这本书应该算是我写的充满快乐感的一本书!”

2010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莫失莫忘》,由凯拉·奈特莉(左)和凯瑞·穆里根主演。图片来源:Allstar/Fox Searchilght
妻子一直都是石黑一雄的第一位读者,创作《克拉拉》时也是如此。“她会在我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创作以后,给我一些让我感觉十分诧异的巨大的影响。”现在,女儿娜奥米也成为了他的编辑。他说,一旦一位作家拥有了一定的地位,编辑们通常都不愿意修改他的作品,担心他会“怒气冲冲”地跑去找另一家出版商。“因此,我非常感激我的家庭成员能够严格地为我把关。”对于拿奖拿到手软这件事,他说,“那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的事情。”哪怕是诺贝尔奖,“当我坐在书房里努力构思着试图写一些东西时,它们(这些奖项)对我的写作毫无帮助。我对于自己何时可看作成功、何时应算作失败有自己的想法。”
石黑一雄创作一部小说大约需要5年时间:通常他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构思,然后快速地写出初稿,他把这一过程比作武士的持剑对决:“开始时有好长一段时间,你一直与你的对手默默对视,你们的身后是被风吹起的萧瑟枯草和阴沉的天空。你一直在思索,然后,就在一瞬间,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宝剑出鞘:嚯!嚯!嚯!接着其中一人轰然倒下。”他这么解释着,一边在视频通话另一头的屏幕上挥舞着一把想象的利剑。“你必须让自己的头脑保持绝对清醒,当你拔剑一击时,你就准确地做到了:嚯!最后这一下必须是完美一击。”当石黑一雄年纪很小跟随父母家人初到英国时,他对埃罗尔·弗林那些虚张声势的电影感到迷惑难解,“在那些电影里,演员持剑过招能够‘叮叮叮’地打上差不多20分钟,而且这段时间他们嘴里还说个不停,”他说,“也许有的人写小说时用的就是这样的方式,一开始就不停地写,然后又不停地改,但我倾向于‘什么都不要写,一切都先放在心里酝酿’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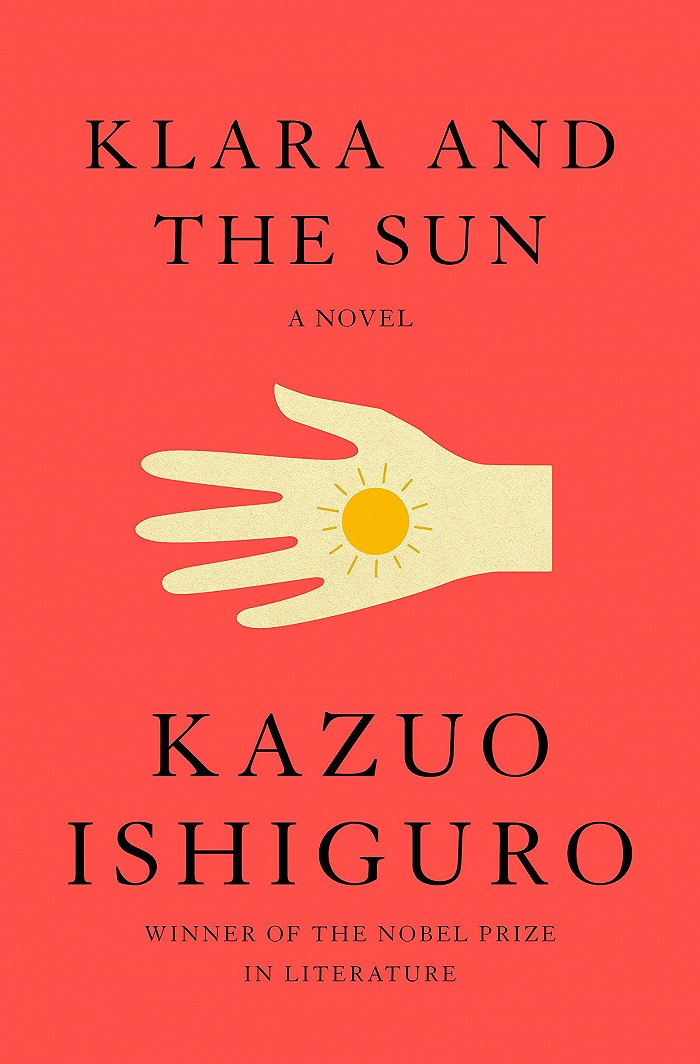
《克拉拉与太阳》
石黑一雄的母亲也是一个在讲故事方面非常有天赋的人,她经常在一家人的餐桌前讲述战争期间的故事(她曾经在长崎大轰炸中被屋顶的瓦片击伤),还为家人表演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些情节。他拿出一本已经破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给我看,这是他16岁时母亲送的礼物。“因为那时的我有发展成为嬉皮士的可能,她就对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你应该读读这本书——读完你会发现你的这些行为是疯狂的。’于是我真的读了这本书,而且马上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对石黑一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母亲给他介绍了许多文学的经典著作。“对于一个对阅读完全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听唱片的男孩,她的说服和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让我相信那些书中可能有些东西确实有用。”
1959年,石黑一雄5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从日本搬到了英国东南部的吉尔福德,他的父亲石黑静南是一位著名海洋学家,当时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合同。石黑一雄把父亲描述为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他认为父亲在科学研究上卓有成就,但对其他事物却如同孩子一般茫然无知,因此他以父亲为原型创作了克拉拉这个小说人物。石黑一雄的父亲退休后,他发明的一台能够预测海岸风暴的机器在花园尽头的一个小屋子里闲置了很多年,直到2016年,伦敦科学博物馆提出将这部机器放进博物馆新建的数学展馆展出。“这件事加上女儿娜奥米也成为了一名作家,令我感到非常自豪。”
石黑一雄的父母在他16岁时给他买了第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但他当时“立志在20岁时成为一名摇滚明星”,他特别希望成为一名创作型歌手,就像他心目中的超级偶像鲍勃·迪伦那样。那时石黑一雄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了超过一百首歌曲,直到现在,他仍然在进行歌词创作,并与美国爵士歌手斯泰西·肯特保持合作,目前他家里有不少于9把吉他。(2003年,他接受了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一项荣誉学位,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能有机会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因为他的偶像也被授予了同样的荣誉学位——“我将在一间布置成绿色的房间里和鲍勃·迪伦一起穿上长袍!”不过那位音乐家推迟到第二年才接受了这个荣誉学位。“我非常高兴能和贝蒂·布斯罗伊德一起获得这个荣誉!”)当迪伦在石黑一雄前一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舆论有些哗然,但是石黑一雄非常高兴。他说:“迪伦绝对应该拥有诺奖,而且我认为像迪伦、莱昂纳德·科恩和乔妮·米切尔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表演艺术家,也是文学家,诺贝尔奖能够认可这一点真的很不错。”
 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在拍摄于1993年的电影《长日将尽》中 图片来源:Moviestore Collection/REX
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在拍摄于1993年的电影《长日将尽》中 图片来源:Moviestore Collection/REX石黑一雄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发表了获奖感言《我的20世纪之夜和其他小突破》,在结尾部分,他呼吁打破艺术的狭隘壁垒,并建议在总体上扩大文学的多样性。“仅仅关注种族问题是不够的,”采访中他澄清道,“正像那个已经被传得变样了的老笑话:BBC可以对任何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取向的人开放——只要他们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当提到他曾在2016年一次电视新闻采访中被介绍为一位“在多元文化的英国里具有标志性的文学男孩”时,他总是竭力强调,对于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或奈保尔的小说里描述的在英国殖民地生活的经历,他觉得自己“游离在这些话题之外”。“我只是碰巧与其他人长得有点不一样,因此我就被归入了这一类作家的行列。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分类。严格点说,我仅仅是因为外表长相被划分进去的。”他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种族方面的多样性,还有阶级层面的多样性。正如石黑一雄所说的,他与同时代的文学家不同,他曾经在一所中产阶级孩子聚集的文法学校和一所当时建校不久的大学就读。
对于记者的各种要求,石黑一雄总是善于礼貌地说“不”,他也总是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防止自己出现“诺贝尔奖综合征”而对世界妄加评论。他描述自己是“一个疲惫的作家,来自智力枯竭的一代”。他的女儿指责他以及他那些思想自由的同行们对当前气候问题的紧急状况显得过于自负。“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做得不够,”他说,“我总是对她说,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能源的使用问题。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花了太多的时间担忧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担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各种主义之间的争斗。我们已经太疲累了,没有精力再去关注气候问题。”《克拉拉和太阳》是他第一部涉及气候变化的小说,不过他承认,这部小说的儿童故事框架使他能够避免过于深陷其中。
他第一次开始担心未来,不仅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还担心在克拉拉那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大数据,以及这些问题对平等与民主造成的影响。 “很抱歉我在这些问题上喋喋不休,”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在改变着它的模式,我确实担心,我们会不会再也无法控制这些事情了。”
石黑一雄希望《克拉拉和太阳》能被读者解读为“一部洋溢着欢快和乐观精神的小说”。但是,按照他的作品的一贯风格,任何慰藉都需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只有通过揭示一个异常艰辛的世界,你才能够向人间呈现光明,你才可以让世人感受温暖的阳光。”
本文作者Lisa Allardice是《卫报》图书版首席记者。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