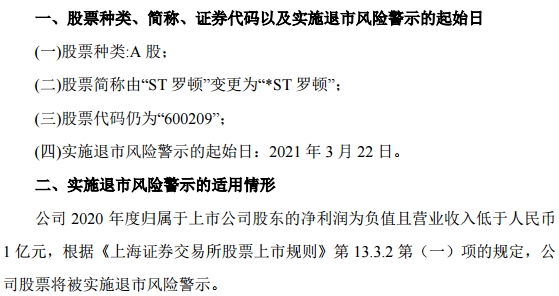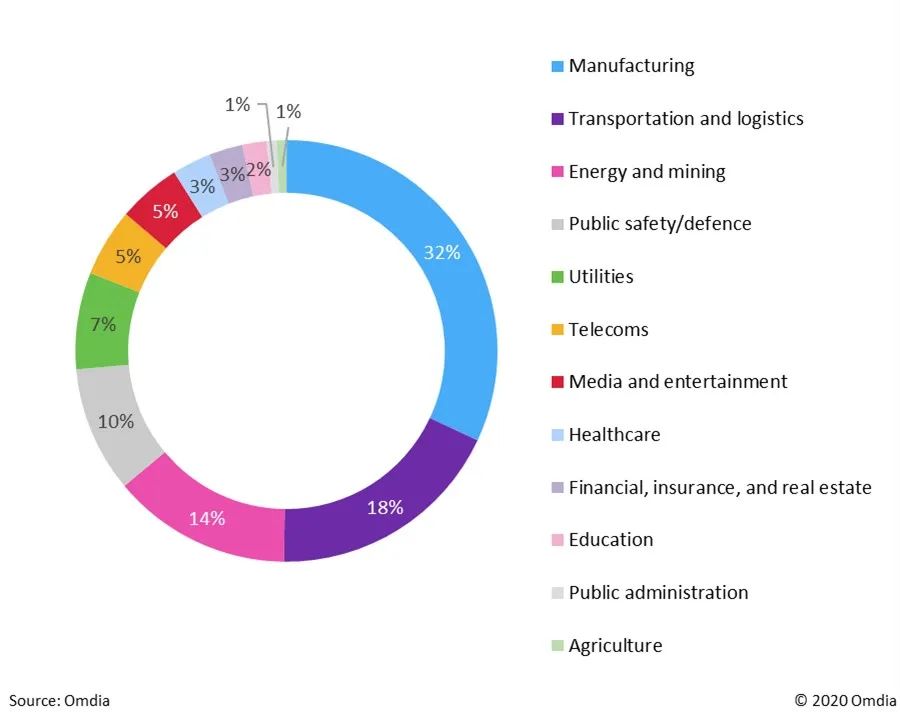原标题:加拿大批评家娜奥米·克莱恩:在全球变暖的今天,无需对孩子们的激进化感到惊讶
 娜奥米·克莱恩 图片来源:drienne Grunwald/the Guardian
娜奥米·克莱恩 图片来源:drienne Grunwald/the Guardian娜奥米·克莱恩带着她于2019年出版的关于绿色新政的书在北美巡回售书活动期间,她和她的助手与当地的“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活动家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年轻的气候行动团体。他们在每场活动中都设有一张桌子,上面放有请愿书和写有行动内容的文件,这样观众就可以现场参与到活动中来。当到达帕洛阿尔托时,他们发现,一直以来指挥“日出运动”的联系人是一个13岁的孩子,她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整个活动。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激发了克莱恩的灵感,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反公司化圣经《NO LOGO》,开始了她的活动。《如何改变一切》(How to Change Everything)是她第一本专门为年轻人写的书。和其他一些书一样,《如何改变一切》试图动员新一代。这些书包括杰伊·格里菲斯的反传统之作《为什么要反叛》(Why Rebel),以及年轻的活动家亨德里克斯·范亨斯伯根的《你该如何拯救地球》(How You Can Save the Planet)等。后者是一本为少年儿童编写的优质实用手册。
克莱恩将她的书称为“活动家的弹药”,她告诉越来越早熟的读者当今世界有三把火:气候变化,不断增加的愤怒、恐惧和反移民情绪,以及年轻人。这第三把火也许能拯救我们所有人。“火花越多,火就会烧得越亮,我邀请你点燃你的火花,”她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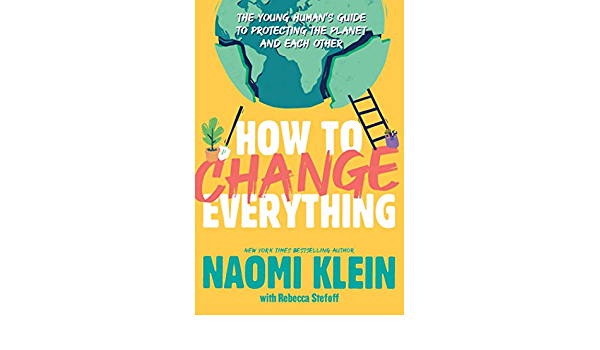
《如何改变一切》
就这一点而言,《如何改变一切》的语气并不煽动,它冷静而详细地阐述了气候危机以及我们能做的事情。对于那些没能从课本里学到气候正义的重要性或碳捕集与封存的缺点的成年人,这是一本有用的入门书。
鉴于克莱恩在过去25年经验中积累的智慧,人们很容易将50岁的她视为最新一波运动的教母。但这样的印象可能会让你误会她是一个爱说教的、不愿意向年轻人学习的人。克莱恩在她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家中谈到,与她在1999年因《No Logo》经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倒性成功”相比,社交媒体让今天的年轻活动家“无比艰难”。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伊尔汗·奥马尔以及其他新一代政治领袖如何应对那么多的输入——包括正面和负面的输入,却仍然能保持他们的想法,而他们做到了。”她认为,部分原因是青年领袖“互相支持”。她举了印度22岁的气候行动(Fridays for Future)活动家迪沙·拉维(Disha Ravi)的例子,她被逮捕并控以煽动叛乱、图谋犯罪。“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全球类似的运动团结在她周围的方式,”克莱恩说,“他们搭建起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正国际化的儿童和年轻人的网络。坦率地说,它的国际主义让成人气候运动羞愧。”
克莱恩对活动主义的看法曾被另一位年轻的活动家托卡塔·伊罗内·埃耶斯改变。当她们在达科他州的立岩地区(Standing Rock)第一次见面时,托卡塔只有13岁。当托卡塔所属的苏族(Sioux,北美印第安人原住民部落之一)社区赢得了第一场反对石油管道威胁供水的战斗时,她说,“我觉得我重新获得了我的未来。”
“这就是人们正在争取的东西——他们拥有未来的权利,”克莱恩说,“这是一个如此深刻的权利,它影响了我的写作。”
 托卡塔·伊罗内·埃耶斯与格蕾塔·桑伯格在一场青年座谈会 图片来源:Jim Urquhart/Reuters
托卡塔·伊罗内·埃耶斯与格蕾塔·桑伯格在一场青年座谈会 图片来源:Jim Urquhart/Reuters克莱恩和其他每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度过童年的人一样,都是在对核战争的恐惧中长大的。很多人——包括克莱恩的家人——都反对毁灭未来的核武器。今天的年轻人的恐惧有什么不同吗?因越战而被征召入伍的美国大学生也觉得自己眼前的未来岌岌可危,克莱恩说。但她认为,今天的年轻人深深感到“不受保护”。这种感受不是源于意外或错误,而是源于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我是在核恐惧中长大的,一切都可能乱套,有人可能会按下按钮,随后我们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而在气候危机中,整个系统只是继续照常运作,但我们会因此走向崩溃。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系统本身需要改变,而这正是年轻人激进化的原因。”
另一个让克莱恩激进化的年轻人是她八岁的儿子托马。“他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她说,“他挑战了我们的消费。我们称他为‘垃圾警察’,因为他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还让我们在家里做堆肥。”
四年前,克莱恩带着托马去澳大利亚工作,并游览了神奇的大堡礁。他们的澳大利亚之旅恰逢一次大堡礁漂白,即全球变暖导致的大规模珊瑚死亡。“我感到既高兴又心碎,”克莱恩写道,“因为我知道,就在他发现我们这个世界的美的同时,它正在流失。”
克莱恩对儿子隐瞒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但最近她已无法让他免受气候危机的影响。去年秋天,托马的学校在新冠疫情期间重新开学,当时该地区被山林大火熏得乌烟瘴气。“老师们面临着这个不可能解决的难题:考虑到疫情,我们是打开窗户保持空气流通?还是关上窗户、保护有哮喘的孩子不受林火的影响?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发现,周围的大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对孩子们的激进化感到惊讶。"
一些家长焦虑如何向年幼的孩子解释全球环境危机。一份指南建议,不应该告诉10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这个星球存在的问题。我的七岁和九岁的孩子在观看大卫·艾登堡言辞激烈的纪录片时,因受震撼而流下了绝望的眼泪。

一些家长担心如何向年幼的孩子解释全球环境危机。图为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山火。图片来源:Joanne Francis/Unsplash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会等孩子长到10岁,”克莱恩说。“现实是,有时我们无法保护他们,因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它正在影响我们的社区。”她试图用托马能理解的方式来谈论污染问题。“我们确立了原则,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后果。而我基本认为,我的角色是给他提供与自然世界发生联系的机会,让他知道自己在为保护什么而战,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出于爱,而不仅仅是恐惧。” 她曾带着他在当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阻止燃气发电站行动。“我试着保护他,不让他陷入无望。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否则我们会让他们陷入虚无主义和绝望。”但她也承认,保护他们是一种“特权”。“这个星球上的很多人没有这个选择,因为他们受到的影响太直接了。想想在中美洲有多少小孩子因为飓风袭击而被迫迁移他们的家园。”
激进主义在今天的年轻化或许是前所未见的,但年长者们已经目睹多代年轻人的反抗都没能阻挡全球的资本主义。年轻人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自己去实现这一切,”克莱恩说,“我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的、跨代的运动。年轻的活动家们很反感一种想法,即,他们的工作就是给老一辈人带来希望。他们牺牲了这么多的童年,做着不该做的事情,这意味着老一辈人更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并从年轻人那里接过属于他们的领导责任。”
《如何改变一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全球性的领军人物格蕾塔·桑伯格。“我在很多方面以她为指针,因为她批判空谈,”克莱恩说,“现在特朗普下台了,有很多政客都在说正确的话。我想到格蕾塔在达沃斯论坛上说的,‘够了,别再空谈了’。让我们着眼碳相关的问题。”
有很多关于新冠疫情将如何改变一切的讨论。我悲观地担心,它已经淹没了青年气候运动,就像911事件淹没了反企业化的全球化抗议一样,但克莱恩相信这场运动会“强势”回归,“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令人惊讶的新策略出现。”
克莱恩说,这场疫情改变的是我们对应对紧急情况的方式的理解。当青年运动呼吁将气候变化作为紧急事件处理时,各国政府的反应是慷慨陈词,而非急迫地行动起来。“新冠疫情之后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知道把紧急情况当做紧急情况处理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政府在这样做。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做出改变。而这是我们这些出生在二战后的人没有经历过的。我们的期望,以及区分‘只是说说而已’和实实在在的变化的能力被提高了,政治领导人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