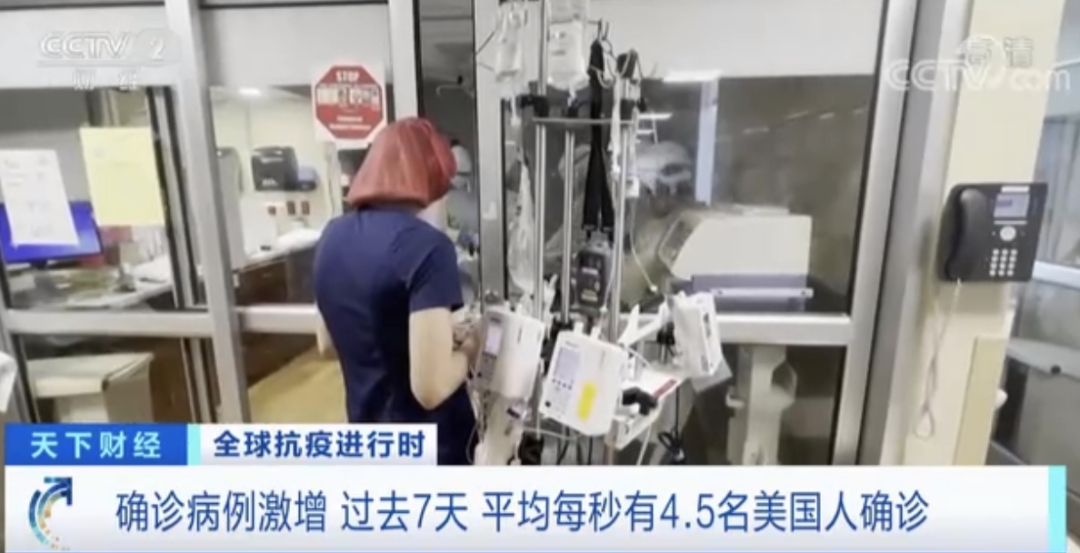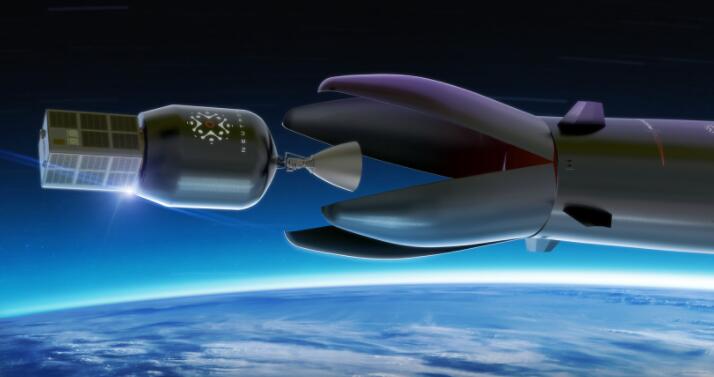身处焦虑的时代
文/艾利夫·沙法克(Elif Shafak)
发于2022.1.3总第1027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愤怒、忧虑、恐惧、困惑、分裂、极化以及对制度越来越不信任和蔑视的时代。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角斗士。我们可以眨眼间互换角色,在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之间来回穿梭。
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21世纪的斗兽场。这些数字竞技场无论大小、不分内外,几乎每天都会上演一场新的较量,尽管争斗双方经常改变,但厌恶和不信任的语言始终如一。古罗马人以他们的野蛮和血腥的场面为乐,而我们现代人只会因为我们的场面而愤怒。
愤怒(anger)这个词的词源很重要,其来自古挪威语angr,意思是忧虑、痛苦、悲伤、痛楚、伤害。愤怒与痛苦直接相关,我们很多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现在都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尽管我们可能不会用这些词来表达。在喧嚣的比赛和普遍的沉默背后,是我们正在受伤的简单事实。
不久前,世界就好像变了一个地方。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乐观情绪盛行。但这是一种危险的近乎自满的乐观情绪。许多评论家认为,历史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线性前进。它的弧线将不可避免地向正义弯曲。那时,“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之类的表述常被使用。潜台词是明天将比昨天更加民主、包容、平等和相互联系。
当时最大的乐观主义者是技术空想家。他们无比轻快。每当他们离开硅谷,参加国际会议或文化和文学节时,都会自信地向我们保证,信息已成为了纯金(pure gold)。这就是我们创造更美好未来所需要的一切。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更多的信息,人们肯定会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信息的快速传播将推翻独裁统治,带来急需的社会变革。
数字平台的发展将把民主理想带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即使是那些闭塞落后的国家,迟早也要加入“文明世界”,这种情绪非常普遍,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脸书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对年轻的埃及夫妇将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脸书”(Facebook)。几个月后,以色列的一个家庭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取名为“赞”(Like)。我经常想起那些孩子,埃及的脸书和以色列的赞。我们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世界?
 美国华盛顿,人们在国会大厦前游行。
美国华盛顿,人们在国会大厦前游行。喧哗与骚动
当然,信息的传播既不能保证也不能产生民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更不用说随机的错误信息和恶意的、系统性的虚假信息,知识却很少,智慧更少。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只关注信息的时候,我们忽视了知识,抛弃了智慧。
信息事关速度,是离散的数据片段、数字。就像“数字”(number)和“麻木”(numbness)之间的差别,不同于节奏(rhythm)和韵律(rhyme)之间的区别。当我们被如此多的信息轰炸时,我们不会去理解我们读到的或听到的信息。持续的信息超载给我们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知识,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渐渐地,我们忘记了怎么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熟悉某个问题,我们可以轻松地谷歌一下,不出五到十分钟,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关于它的东西。再多花几分钟,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相信我们是专家——即使这些信息片段并不等于知识。
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每天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增加我们的知识,最终增加我们的智慧呢?为了获得知识,我们需要放慢脚步,提防教条,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教条。我们需要起身离开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知识需要书籍、跨学科阅读、慢新闻、深入分析、细致入微的对话、避免草率的判断。而智慧则需要我们将思想和心灵结合起来。要获得智慧,我们不仅需要纯粹的理性分析,还需要情商、同理心、谦逊感和同情心。
我们需要倾听彼此的故事,并关注沉默。
慧根
疫情伊始,伦敦人还可以在公园散步,我注意到到处都张贴了讯息。“当这一切结束后,你希望世界有何不同?”他们问。在问题之下,路人用笔潦草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有人写道,“当这一切结束后,我想生活在一个我可以被听到的世界。”
在一个数字平台和自由民主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传播的时代,我们理应都拥有发言权,一个悲哀的讽刺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无从发声。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他们知道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负面情绪,并且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或疏导它。但我们不喜欢谈论它,尤其是在我的第二故乡英国,在那里表达情感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绝对不能在我的家乡土耳其,在那里许多人认为女性是感性动物,而男人更理性(这当然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都是情感动物。当我们彼此联系时,是通过故事和情感。我们所信仰的或为之奋斗的,取决于故事和情感。即使我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们也会通过故事和情感来记住和留存一些东西。
我一直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是原始能量的来源,就像一种可以加工成各种形式的矿物,一种可以被塑造成不同形状的金属。与其试图压抑我们的情绪,不如承认它们的存在,公开谈论它们,并创造包容性的空间,让我们可以理解和探索我们的心理健康如何被困住,这样似乎更加健康,或许更明智。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不被认可也完全是可以的。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担忧或不快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生气或苦恼,恐惧或沮丧,而是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些情感。我们能否将本真的情绪转化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东西,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社区和社会都是如此。
归根结底,如果有一件事比任何情感都更具破坏性,那就是缺乏所有情感:麻木、冷漠、精神萎靡。当我们对泛滥的信息变得如此麻木,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去注意世界其他地方甚至隔壁在发生什么时,我们就被彼此完全隔绝了。这是一个危险得多的门槛。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对地球、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持久的影响。现在我们可能还处于焦虑的时代,但从这里到冷漠的时代只差短暂而致命的一步。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跨出这一步。
流动的时代
许多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和写小说时,一位美国学者采访了我,她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研究“中东的女性作家”。我们聊得很愉快,她面带柔和的微笑告诉我,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土耳其人,并且我在土耳其。她说话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她看不到自己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任何理由:她来自美国,一个妇女权利已经实现的国家,并且美国的民主是稳固、稳定和安全的。
然而,自2016年以来,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变得不再顺理成章。在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兴起、自由民主遭到侵蚀,以及与极权主义没什么区别的“反自由民主”出现之后,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性观念,甚至在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心中也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坚实”国家。用已故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创造的术语来说,我们都生活在流动的时代。历史并不一定是直线前进的。如果说现在是流动时期,那么随着疫情、气候危机以及社会、数字、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平等现象的扩大和深化,这股潮流似乎加快了。
这是我们需要全球姐妹情谊、全球团结的时刻。无论我们是牙医、学生、工程师还是诗人,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没有冷漠的奢侈。从另一场疫情的可能性到环境灾难,从网络恐怖主义到难民危机,前方面临着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都无法用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部落主义或群体自恋的修辞来解决。
我们必须接近自然,理解我们对地球的责任。我们必须相互联系,努力成为敬业、参与、有知识、有智慧的公民。沟通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
故事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根深蒂固的沉默使我们分开。
我们的声音可能不会被当权者听到,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也并非无话可说。我们有能力改变世界。
(作者系土耳其畅销书作家,其作品包括《伊斯坦布尔小人》《伊娃的三个女儿》和近著《失踪树之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