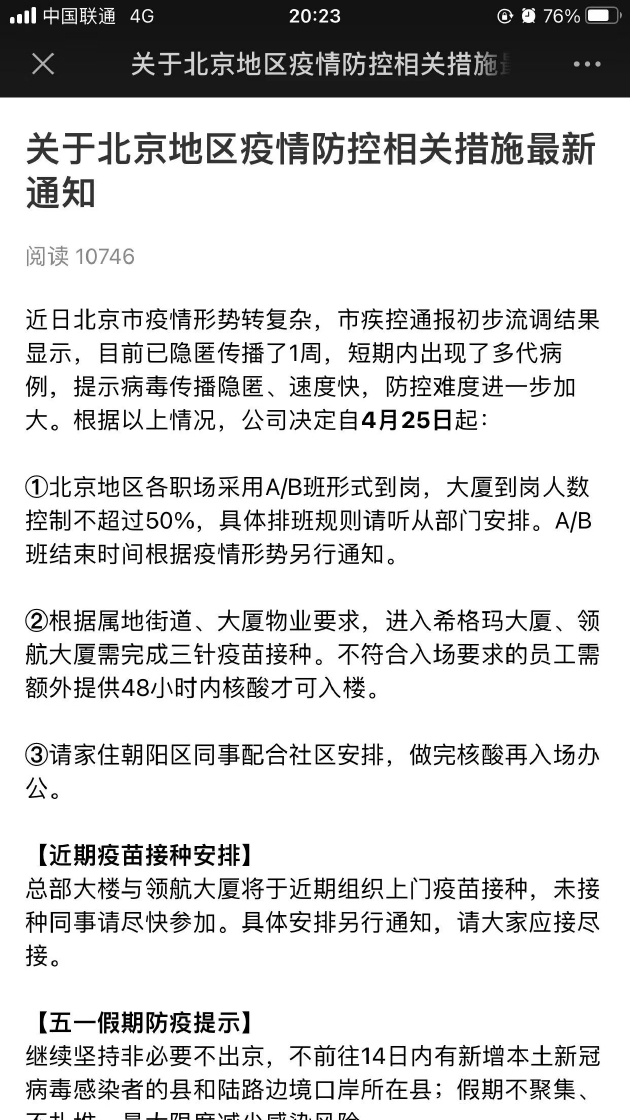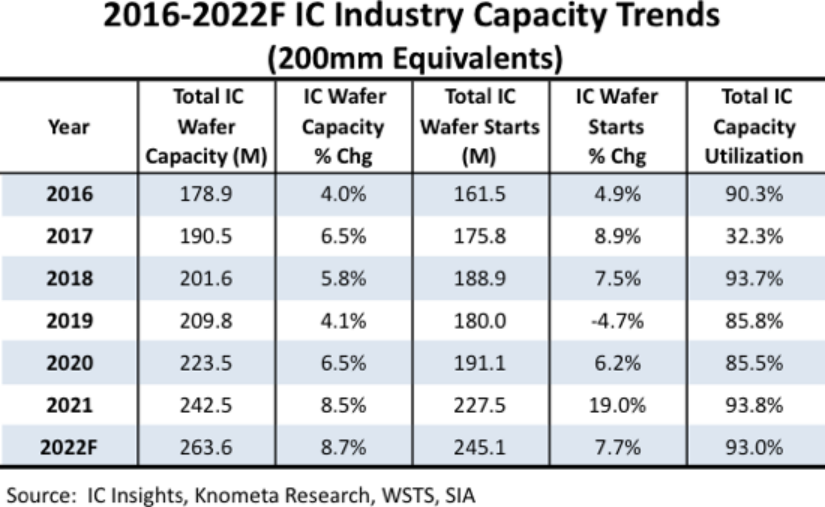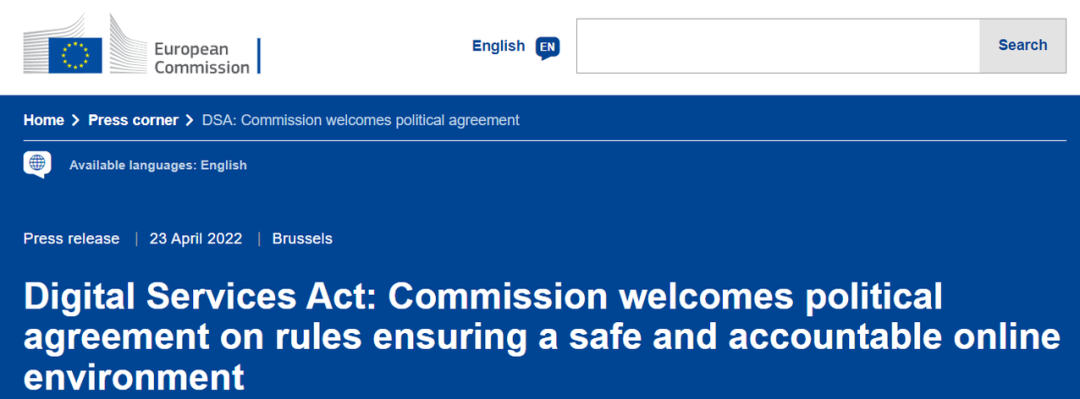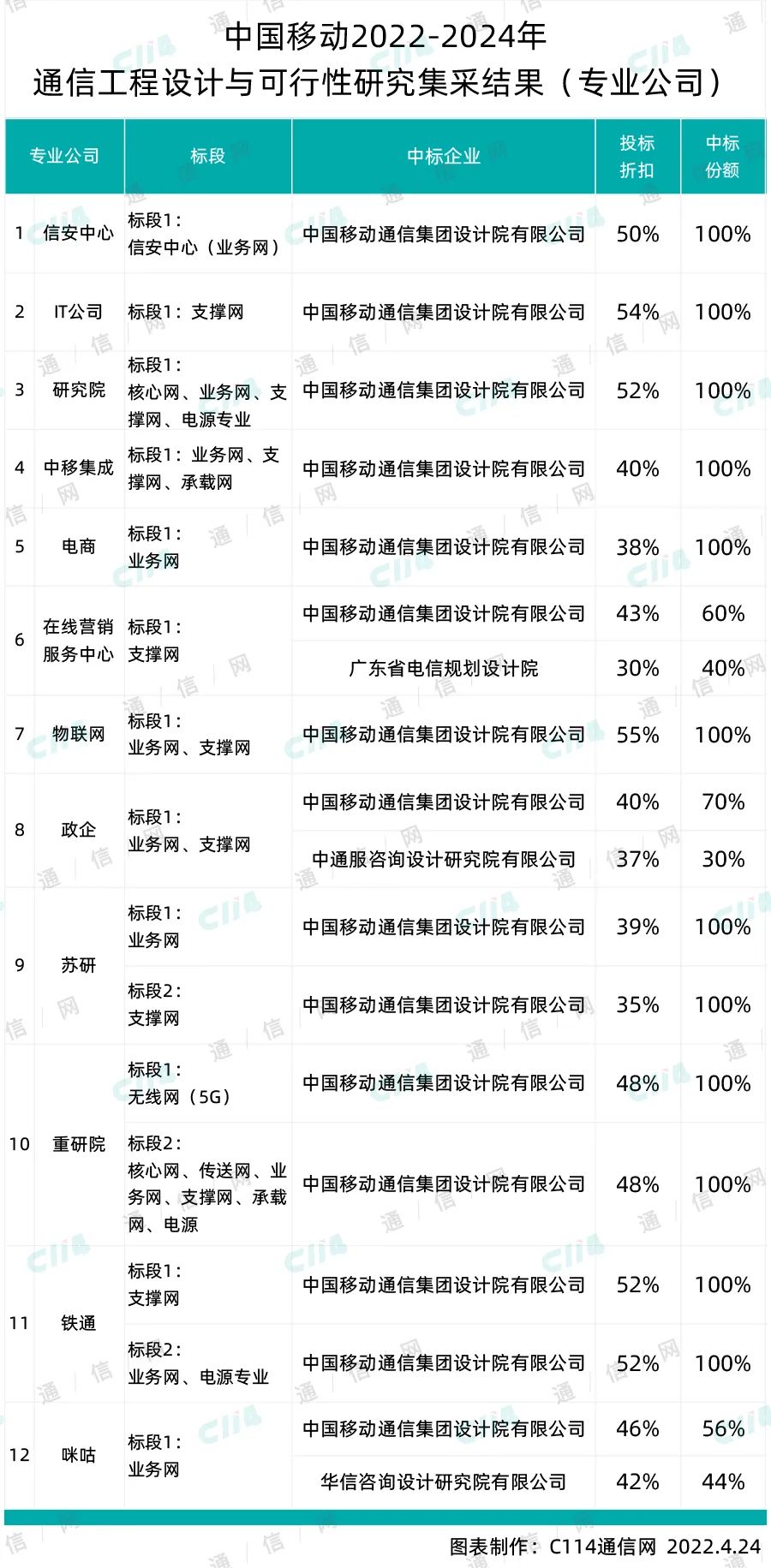■一点表里
·米肖
在明代,一个常年有奉禄拿的朱姓王孙家族里,出了一个反骨少年。在很小的年纪,这个天才少年便能吟诗了,喜不自禁的父亲竟然拿小小的他与杜子美作比。这个聪明的少年,十五岁起自愿放弃王孙地位和一生坐享其成的奉禄,去考场应试科举,也居然中了秀才……因为生就一双大耳朵,所以,家人取名曰“朱耷”。古人都把有一双大耳朵看作是富贵有福的象征。
这个少年不负众望,果然英才。
然而,就在朱耷考取“秀才”以后,人生的绸缎尚未完全铺展,才华尚未得以继续施展,命运突然来了一个转折,时代的大潮席卷一切———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一时,明朝江山崩了盘,围剿朱姓王孙势在必行。昔日享尽荣华的王孙们,有的一家九十口,全被灭门;有的所幸跑得快,加入到流浪大军里。
朱耷也不例外,他携妻带子东奔西突,苟且生存。一日,一家三口来到某处空旷院落,饥饿难挡,朱耷自告奋勇找吃的去,让娘儿俩不要走开,等他回来。哪曾想,这一别,竟成永决———朱耷吃的没讨着,自个倒迷起路来。往后,再也没有与妻儿团聚。
后来,南昌街头的人们,常看见一个伏地痛哭的男子,或者仰天大笑的疯男人。他便是朱耷,这个放弃了王孙奉禄一身反骨的人,在一夜间妻儿离散,天崩地裂,无家可归。
哭也哭过了,疯也疯过了,接下来怎么办?清兵入关,是要剃头的,当时有“留发不留头”的酷刑,对于那种剃光半边脑袋,于脑后甩一根长辫的奇怪发型,朱耷是难以接受的,于是,辗转逃到山里,索性把所有的毛发全部剃光,坐起和尚。
一个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人,他若不死不疯,那么,去深山面佛,则是最好的缓冲。
由于自小聪颖,能书擅画,面佛参禅之外,自是专攻此道。起先,我对朱耷的书画没有感觉,谈不上欣赏。后来,得知他的身世,仿佛开了一个小口子,一下子懂得了他的笔法。
先看他的书法,粗疏有致,分明含有恨意在里头,但是,这种扭曲的情绪又适时被朱耷的修养给调和了过来,成了明月花道轻风徐来。一个有底蕴有血泪过去的人,是深晓用力的,但,有时,过于急迫,反而欲速则不达。绘画也如此,只有等到一根心弦稍稍放松下来,便什么都好起来,纵身一跃,终于到了另一层境界。
看朱耷的书画,尤其后期的,有了忘我之念。他彻底把过去忘了,将整个身心融入自然之中。他画了那么多的鱼鸟图,每一条鱼都翻着顽皮的眼。一只墨色呆鸟站在悬崖绝壁处,水里的鱼儿翻着白眼望着岸上的它,心想———你倒不如我,虽有高阔天空的自由,可我一生藏于深海,不见得比你失去的多。就觉得那些鱼,是朱耷不同的化身,他小半生埋首深山古寺,偶尔云游四海,结交友朋,切磋技艺。古代的和尚多是隐士———所谓隐士,就是隐起来的士,饱含才华,手下笔墨酣畅,他们隐起来参透人生,个个身怀绝技,朱耷不过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他还是朱耷,直到看见徐渭的窄卷长轴,自叹不如,方才钻研临摩,费劲心血,那一个阶段,始终没有走出“前辈徐”的阴影。艺术永远如此,它可以把人吓住,从此萎谢;它是光,可以把一个人的双眼刺瞎,除非你独辟蹊径。好在,后来,朱耷终于走出来,并且有了自己的路。那个作为王孙贵族的朱耷从此消逝了———八大山人横空出世。
他有许多身份,面佛参禅的高僧,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看他的竹石图,奇崛怪瘴,一墨黑,深不见底,只稍微探几根竹枝过来,一扫人生的沉闷之气。他终于从小我的情绪里拔出来,走向了更为广深的天地。他的生命里,没有了妻儿温馨,唯有古佛青灯,一双茫鞋踏遍苍绿山水,一个把身心皆敞亮地融入到自然的人,是有福的,没有了小我的羁绊,像一尾鱼游于大海———万里如海一身藏。
特殊的身世,高深的修养,使得八大山人有了一种孤绝的气质。在他的晚年,他的画并不能为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所喜爱,他也不必去迎合他们。
晚年的他,靠卖画为生,日子该是何等清贫。一个县老爷也算激赏他的才华,前来索画,并要求一二三什么的,可他偏不依照来人要求,使得“当事人”无可奈何。曾经,他跟一名为官的朋友翻脸,且画了一幅孔雀图———那两只著名的孔雀一点也不美,偏偏鼓起腮帮子生气,羽毛收在尾下,简直不如一只普通的鸟好看。这就是八大山人为人的倔,不屈服,不奉迎,浑身是刺,让别人不痛快,处处树敌。我从孔雀图里倒能看出他的一脉天真,历经复杂身世,始终不懂得低头就犯。然而,还是这脉天真搭救了他,使得他有了从朱耷到八大山人的蜕变。
文人隐士,向来如此,他们始终有一脉天真的眼,不在世俗里妥协,像八大笔下的一尾尾鱼,翻着白眼冷窥人世,以顽皮的姿态决裂,然后逍遥深海,冷暖自知。
就是这么清贫而修养高深的老人,竟也高寿,逝于耄耋之年,可谓得愿其所。时代磨折了,也成全了他。妻离子散后,没有疯癫,是命运给他的恩赐,以致后来,他在书画技艺上走得那么深远,这又是命运对这个长着一双大耳朵的人的额外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