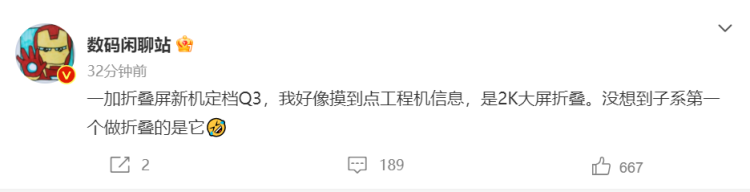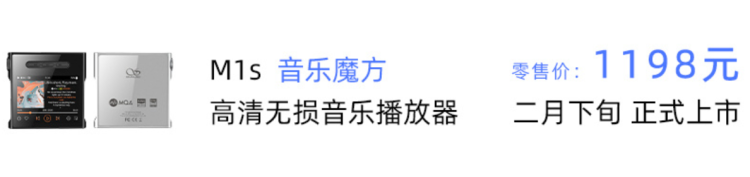今天,分享一篇诗来使我感旧事,希望以下诗来使我感旧事的内容对您有用。
■生活 米肖
春来,连日阴雨,走在户外,每见路上一个个小水坑,我总是条件反射想起北岛那首《雨夜》,简直可以倒背如流: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当灯光串起雨滴/缀饰在你肩头……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揉着你的头发/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路灯拉长的身影/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
多年来,一直克服不了,仿佛一种本能,好比幼童时期打针,当那种锐尖的铁器突然戳进肉里,总是痛得情不自禁哭出两个字———妈妈。人类在极端恐惧的无助状态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母亲。每当我看见小水坑,北岛《雨夜》中的诗句总是适时冒出来,压都压不住,这大约就是典型的诗歌综合征吧。让人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间段里。套用上了岁数的人的口气说一句,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年代。
一个少年忽然辍学,跟着家人自乡下迁居城里,被粗暴地抛到社会,于工厂流水线上前行着枯燥乏味的工作。应该是《朦胧诗选》救了她。舒婷、顾城、北岛、杨炼、芒克们的诗篇,将一个少年的精神世界慢慢填充着,也算起到了文化启蒙的效果,使得她先前的八年义务教育都化作了零。从舒婷、顾城的经历中,她似乎也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们两个人分别为高中学历、小学学历。有什么可怕的,他们照样立足于社会。置身一段可以独自给自己取暖的年岁,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年岁———从一段段分行的句子中发现了火与光,默默用来照耀自己。
至今,我似乎还会背杨炼的《诺日朗》: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强盗的帆向手臂张开,岩石向胸脯,苍鹰向心……牧羊人的孤独被无边起伏的灌木所吞噬/经幡飞扬,那凄厉的信仰,悠悠凌驾于蔚蓝之上/你们此刻为哪一片白云的消逝而默哀呢/在岁月脚下匍匐,忍受黄昏的驱使/成千上万座墓碑像犁一样抛锚在荒野尽头/互相遗弃,永远遗弃:把青铜还给土、让鲜血生锈……
一句句,一行行,飞天一样超凡脱俗,金属一样掷地有声。
前不久,听一场诗歌朗诵会,当到了舒婷的《祖国啊,祖国》,精神层面的那个我几欲热泪盈眶,那是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记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一批女诗人中,可能数舒婷最大气,没有一味将自己浸淫于个人情感的书写中,而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然而,当我知道北岛便是赵振开的时候,他早已去国日久———那个时候,我的小小的人生观与时事观慢慢有了雏形,是社会的风雨、个人的历练的双重夹击所致。一个能将一首诗读得热血沸腾的年岁,是永远充满活力与生机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自费订阅《诗歌报月刊》。每月上旬,总是去小城邮局小卖部去取。彼时,朦胧诗派渐渐式微,我们开始接触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韩东的《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说真话,读这些人诗歌的时候,那种神圣感突然消逝了,滋味相当滑稽,仿佛在教堂祈祷时突然笑出声来,一种宏大庄严的气氛,忽然被这些新生代诗人们集体消解掉了。至今我也说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否有了识别之心,可以擅自淘洗甄别?也不全然,这一直是个谜。
唯一对女诗人蓝蓝的作品情有独钟,我一直作为她的忠实读者而存在着。一位能将诗还原得那么简洁的女子,几十年如一日,初衷不改。如今,偶尔看她的诗,依然闻得到那种熟悉的气息———光阴对于她的内心,构不成任何威胁。偶尔回小城,看见书柜里那些几十年前的《诗歌报月刊》,总是一种“谓我心忧”的惆怅。一个人独自活在一种文体里的时间。
有一阵,非常喜爱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每日抄读几首;或者看电影的时候,突然听闻话外音里穿插着朗费罗的诗句,一颗心激动到颤抖的程度……那都是些值得珍视的过往。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我重新回到本原,回到“白日依山尽”的起点,开始读那些存在千年的古体诗,一个诗人一个诗人地读下去……连时间都起了灰尘,我依然在这里读诗。